《银饰》剧照
《银饰》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民国年间。道景(王同辉 饰)是江阳县知事呂敬仁(王庆祥 饰)的公子,此公子有两大癖好,自幼对女人不感兴趣,单与貌美男子狎猊,并有收藏女性衣饰及精美银饰怪癖。其妻碧兰(孟尧 饰)婚后等于守活寡,她对丈夫的淫匿行为深恶痛绝,不甘白来人世一回的碧兰终于红杏出墙,与宣恒银饰银匠少恒(谷洋 饰)好上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此事被公爹吕敬仁察觉,他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想招。这天,他以明德府内女眷做银饰为名,让碧兰将少恒请入府内,密谋毒死少恒,然后嫁祸与其偷情的碧兰,再借老银匠(严顺开 饰)之手将碧兰除掉。一切如愿后,闻讯的道景赶回家中,他从行将自尽的老银匠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万念惧灰的道景身着银饰女装,走向了亡妻的坟头……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沙发上的马勒真相漩涡一夫一妻制奈河非常绑匪俺娘田小草后菜鸟的灿烂时代斯嘉丽小姐和公爵第三季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代号:皇帝军民大生产周围的事杂技皇后夏菊花地狱之旅杀戮游戏High到哈佛魅魔小小心愿人生访客美丽的青春灵异妙探第八季类人猿行动劫后重生之宝藏之谜明日方舟:冬隐归路令总无恙心密码狗之车旧案寻凶神的病历簿2死亡令我重生
《银饰》长篇影评
1 ) 欲望的诉说——电影《银饰》解析
黄健中的电影《银饰》改编自周大新的同名小说,电影里出现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远去的年代,封建的县城,幽闭的大宅子和压抑的人性,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隐秘的东方故事,而电影中不断出现的腊梅、银饰和戏曲等符号又将这个中国故事渲染得十分妖娆和吊诡。
在这个电影里,不仅仅是一种东方式的猎奇,更有对欲望的解读和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反思。
欲望之源头——三个主人公欲望是对能给以愉快或满足的事物或经验的有意识的愿望,每个人都有欲望,或者是落到实处的实物,或者是想要实现的想法。
对于一个基本的人来说,人本身就分为男人和女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性欲,两性对于性的渴望是一种本能,然而这种源于生理的本能在电影里却成为束缚主人公的原罪,甚至导向了人物的毁灭。
最直观的就是电影主角碧兰夫人这个来自女性对情爱的欲望,这位十六岁就嫁入官宦人家的体面人,却是内心苦闷不堪,因为丈夫的性别错乱,碧兰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该有的情爱,她控诉自己的丈夫“咒骂我,用烟头烫我,用簪子发卡刺我”,从刚开始碧兰的面无表情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生活,面无表情既是大户人家的高冷,更多的是被压抑的人性使然。
然而这看似平静的背后却暗涌不断,她暗中买砒霜来结束这样的生活。
寻死失败后遇到小银匠少恒才真正享受到鱼水之欢,两人做了一对露水夫妻。
对于电影中的丈夫吕道景来说,欲望不是性欲,他是一个人,他有希望被认同的欲望和想要被爱的欲望。
不管是来自妻子碧兰的指责“他不是个人,不是个男人”,还是来自父亲吕敬仁的咒骂“贱、贱种”,吕道景身上充满着不被认同的痛苦。
这些不认同者当然不会给予他应有的爱情和关爱,不仅如此,甚至对于心爱的男人铁头也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
来自家庭的疏离和社会的抛弃都构成了吕道景的生存图景,既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同,也得不到梦想的爱情,只能在戏剧里反串和半夜的易装才能得到所谓的“舒坦、安逸”。
电影中的另一个人物身上也隐藏着一种欲望,出场较少的吕敬仁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家长和县城的大老爷,他既是父亲,也是权利的代表。
作为父亲,他不能接受性别错乱的儿子,不能接受红杏出墙的媳妇;作为父母官,他不能允许儿子乔扮女装,所以他才说“天呐,为什么让我生下你这个贱种”,作为县城权利的中心,他要维护自己的体面,所以他不允许儿子出走流浪,甚至教导自己的儿子,“人要学会抑制自己,世上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欲望,但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学会抑制自己”。
他要维护家庭的体面,所以他不动声色地下药毒死小银匠,嫁祸给碧兰。
他要维护的是名声和面子,维护的是自己的欲望;他代表的明德府其实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是悬挂在书房的“纲常、名教、道德、文章”。
所以他要求儿子“要学会掩饰,要学会背着人做事”,这关系到声誉、身份,他处心积虑地杀掉小银匠和碧兰也是维护声誉和身份。
欲望之意象——两个物象电影是表现的艺术,通过镜头的调度运用、景别的选择、色彩的调试和音乐的搭配,来传达导演的意图。
整部电影最有象征意味的莫过于反复出现的腊梅和贯穿始终的银饰了。
电影第一个镜头就是一片腊梅林的近景,女主角碧兰夫人由远及近走入镜头,腊梅严冬独自盛开,本身就带有悖逆主流色彩的叛逆形象;“孤根独暖”的特点又点明了潜藏的生命的欲望和压抑的孤独;“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更像是对世俗和社会的控诉,徒有光鲜的外表和生活排场,让这个空有“好颜色”的女人更希望得到情欲的满足,更希望绽放生命的欲望。
腊梅香又直接关联着女人香,小银匠和碧兰在腊梅林里的几次交姌都是原始欲望的释放。
电影的始终贯穿着银饰这条线,银饰对于碧兰来说,是得不到丈夫情爱的压抑,是来自世俗的束缚,最终她突破了捆绑,她的首饰都摘下来送给了丈夫,在小银匠那里满足了欲望,得到了情爱。
银饰对于吕道景来说,代表女性的柔美品质和身份认同,也代表了来自人性的压抑和束缚,最终他不断得到银饰,却在这种束缚中窒息。
最后,传统诗意的腊梅和传统手艺银饰的制作还构成了整个电影的文化背景,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给电影带来了传统的美感和诗意,又有来自传统的残忍覆灭,碧兰和小银匠在腊梅林经历了生命的绽放,也极速走向毁灭,碧兰在银饰项圈的套牢中死去,吕道景也在一片腊梅下的坟头戴满银饰死去。
可以说腊梅和银饰将整部电影完整地串联,又内化为一种电影手段,为主题服务。
欲望之结局——走向毁灭几个人的美好愿望,碧兰希望老爷不再做官,道景和她离婚,她和小银匠在一起;小银匠希望能带上碧兰跑,没有官府;吕道景希望能流浪出走或者出家,离开这个现实束缚的牢笼。
这些都不过是主人公一厢情愿的幻想,不可能实现的泡沫。
在传统世俗的眼中,性别错乱症、异装癖和婚外恋都是不被允许的,虽然最终被明德府的老爷悄悄处理,但这里可以看作是传统世俗和封建伦理对欲望的扼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毁灭的导火索其实还是欲望,正是欲望促使吕道景要求碧兰定期提供银饰,也是欲望促使碧兰偷窃官银被发现,还是欲望使得吕敬仁痛下杀手。
缘起欲望,缘灭还是欲望,欲望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乐,也是最终的毁灭,电影最后明德府依旧庄严肃穆,不得不说让人唏嘘不已。
电影讲述的悲情故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在第五代导演中,我们不难看到讲述两性、压抑和欲望主题的电影,包括《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等等优秀的作品,第五代导演的相关主题电影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黄健中的这部《银饰》为什么不能得到同样的地位呢?
很大程度上,《银饰》还在用电影语言来讲述一个传统的、老旧的主题,虽然披着情色、悲情、同性的外衣,但是电影本身还没能将欲望的主题挖得更深入,对人物的把握也不够深刻,例如主角之一的吕道景的内心就表现得不够复杂,没有着重刻画。
没能从传统文化的反思角度走得更深,是这部电影的缺陷之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
2 ) 这个电影有点无聊的
不知道表达什么东西,整个电影除了女主角露出2个巨大的mm让男的亲,其他不知道有什么可勉强吸引人眼球的。
无聊的要死。
3 ) 吃人
难以想象中国在伦理片上有这样的艺术佳作,导演在探讨同性恋,出轨,旧中国社会体质上游刃有余,体现了对作品超高的品控。
是难得的伦理片佳作。
导演在情欲戏上的功力也是不得不说,将一个性难自抑的女性在面对心上人的人时的主动让我不由得想到李安在喜宴中对老外表达到你正见识到中国五千年以来的性压抑的结果。
最后在仆人给“明德府”描金又是一处嘲讽僵化的体制吃人的妙笔~
4 ) 当《银饰》变黑的时候
全面采用了数字拍摄设备的《银饰》,竟然像极了一部二流拍摄水准的电视剧。
手法的陈旧,表演风格的模式化,令人大跌眼镜。
如果说这是一部被雪藏十年以上的旧片,我看也是只能理解不能原谅的。
黄健中至少赢得了两项骂名:刻意制造情色画面做为抄作卖点以及暴殄天物般地使用高端电影拍摄技术。
一波又一波的恶评使我想起了小银匠的老父亲不慎将碧兰送给他的银两掉入参汤之中变为黑色的场景。
“啊,啊,有毒,参汤有毒!
我的儿子是被碧兰毒死的啊!
”老汉的肝肠寸断,如何能不让人为之揪心。
但这样的一个发现,难道又不是对电影本身的讽刺?
从影片的故事情节不难判断:《银饰》一定是一部优秀的小说,然而《银饰》却终于在光影世界中变成了黑色。
5 ) 隔靴搔痒
最近看了一部片子《银饰》,一个缘由是该片号称中国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那可是主仆偷情的经典作品啊,大学时候看得VCD,导致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幻想着有钱了要雇个保姆,然后再发生点什么美好的事情。
另一个噱头是因为导演是黄健中,《大鸿米店》就是他拍的,偶还记得里面一个长工饥渴的在仓库的米跺上面睡觉,滚着滚着就high了。
看了之后,偶发现导演肯定是被冤枉了,偶打心底相信导演是清纯小男生,是无辜的。
好比报道说某人是个大厨,最最擅长女体盛,结果后来发现该人进了厨房,拿着没开刃的菜刀切菜,甚至不知道如何点火打开炉灶。
片子的情节很俗套,偏远的乡土小镇,官宦之家,大少爷是同性恋,喜欢穿花衣服,戴首饰,演戏,看上了挑水的铁汉哥(这个名字非常有阳刚之气);于是少奶奶嫁入豪门多年却还是个姑娘,情挑小银匠,多番的XX之后东窗事发,主角们都一个个悲惨的死去。
开场,少奶奶去小银匠店里试脚链,高叉的旗袍都快到腰了。
小银匠颤抖的双手扒下长筒袜,乳白,乳白,恨不得扒上去啃一口。
腊梅林子,小银匠扒在少奶奶身上,一路搜寻着香气,几经提醒才意识到是乳香,狂扒一阵,背上披着披风,就XX了,可惜身体蠕动的样子非常不自然,偶十分怀疑该小银匠还是个新手。
晚归,小银匠被他老爸(严顺开演的)审问去干了啥,“啥也没干”;“胡说”;“她跟我说了很多话”;“然后呢”?
“她突然扑在我身上”;“然后呢”?
“她说要要我”;“然后呢”?
“于是我们就做了”。。。
该个桥段倒是在H电影中不多见的,还算有些心意。
严顺开果然是牛人啊,大陆小品界也是说北有赵本山,南有严顺开,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他在某年的春晚上演的小品,上海小阿三。
结尾小银匠快死了,还不住的叫奶,奶。。。
于是少奶奶解开衣衫,红红的肚兜下一个小点,偶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肉体的突起,还是衣服的褶皱,镜头就闪过去了。
晕,谁说里面有露点镜头的??
演的人是穿着裤子上床,看的人是隔靴搔痒。
6 ) 很期待《银饰》里这样的女人...
我一直觉得碧兰就是一个长期饥渴没有受到滋润的女人猛然遇到甘露便死不撒手的那种...敢说碧兰对少衡的感情,是爱情么?
不是,绝对不是。
而是肉体磨合之后产生的一种依恋之情。
我突然想起了大学思想品德课里对爱情定义的三个要素:理想、责任和性爱。
这部电影里只具备了性爱这一个因素而已,谈不上其他。
但关键就是这一个因素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
张爱玲原著李安导演的争议电影《色戒》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么。
7 ) 《银饰》结局的五种死法,你更欣赏哪种?
本来是冲着情色片来看,没想到却是这么个悲剧,开头各位都好好活着,最后竟一连串死掉五个人,主角、主要人物全死完了,连还没生的都死了。
结局五个人死掉,一共五种死法:少恒:含笑而死。
最后还能享受香乳,最后吃奶的力气都没了时就死了。
当然,他难免有一死,从他这个小工匠偷攀上贵妇人家时就注定会有一大劫,这一点不管他自己想不想得到,都是那个等级社会的宿命。
碧兰:含怨而死。
被少恒的爹错怪报复而死,而且起初还以为是少恒送的银饰项圈。
这种死是够悲惨的了。
少恒的爹:含悲、含恨而死。
悲,是悲其子死得早,死得怨;恨,是错恨碧兰。
吕道景:含愤而死,也是含笑而死。
愤,是愤其家庭,害死了碧兰,以及造成了整个悲剧;说是含笑,则是他自尽于碧兰坟前时面带笑容。
碧兰肚中孩:还没生出来就死了。
这个片子其实始终没有打动到我的“悲情”,甚至有几个地方我还忍不住笑出声来(比如少恒他爹刚开始盘问少恒那段、道景他爹训道景那段)。
但我承认这个片子在思想情感上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
我本来不打算想太多,更不打算写此影评,但没想到看完这片子,睡后第二天,想法多起来(也许是因为该片很有思想性)。
我觉得仅从现实的角度考虑,这片子里的人物都不算悲剧,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很不错,人生欢乐事都充分体验过了(除了道景),虽然大多死得充满遗憾,但其实生前活得都挺不错的。
像碧兰、道景,都挂靠在或生长在权贵人家;少恒及其爹,也是生活宽裕的熟练工匠阶层-小资产阶级,也不是悲惨的劳苦大众,就算悲惨,起码有过人生欢乐也死而无憾了。
在上述背景下,这场戏如果要说是悲剧,那么就主要是思想、感情意义上的评判。
这种评判在残酷的现实社会来看,到底还是奢侈的。
因为显然,对于那些生存都很艰难的阶层来说,这些感情、个人幸福的实现与否,真是连想像的力气和心思都没有。
但是要抛开现实来说,就看个人感受,银饰结局五种死法,哪种比较好呢?
你欣赏哪种?
——我深思后发现,这两个问题看似一个问题,但我却有不同的回答:首先哪种比较好?
纯粹从个人感受来说(包括实际生活的和情感上的感受),我会觉得少恒比较好,因为他的生活过得不差,凭手艺吃饭,而且又享受过了男欢女爱。
虽然他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他可以大致明白的,他最初选择与碧兰偷情时就注定了完蛋的风险),但是他活得很好,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死还死在浓情蜜意的温柔乡里。
但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评判,少恒的死法只是一种很个人的、而且很傻的死法,因为他的死是因为他个人偷情、违反传统伦理而必然遭到的社会迫害结果,纯属个人悲剧,而且从影片来看,少恒自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于非命,影片中的少恒始终是个天真的傻小子。
我更欣赏的是道景的死。
可以说,他在亡妻坟前自尽、华丽而死的做法让我比较意外。
这种自杀既带有对个人特殊情感未能在现世中实现的反抗意味,更超越了个人,带有对家庭、对社会伦理的抗议。
也由于意外他最终竟以死抗争,我又回想了这个影片并没有给太多镜头的人物之前的经历,这样一个懦弱软弱的边缘人,最终却是思想上最激进的抗议者。
在影片中间,当道景以获取银饰为交换、默许碧兰与少恒的偷情后(这本身有点变相“性交易”的意味),道景与碧兰长达七年毫无感情、只有相互精神折磨的生活,反而戏剧性地开始产生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或类似于“惺惺相惜”),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道景对碧兰开始萌生某种怜爱和珍惜的感情,至少也是某种特殊的友情。
当然道景的人生与少恒的人生相比,在物质和精神相匹配的意义上来看要糟糕得多了,道景从小到大都活得很压抑,不像少恒那傻小子实在是无忧无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我当然不会认为道景的人生更好。
然而以现实类比,很多人不正是长时间地活得很压抑?
在压抑的意义上,很多人不比道景好到哪去。
大多数人都平庸地死去,很多人憋屈地死去,而在其中,那些抗争而死的人,哪怕是少数,难道不更值得欣赏吗?
也许会有更消极的人,会觉得碧兰肚中孩的死法更好:觉得根本不应该来这个世界。
其实偶尔我也会这样想。
不过我还是想,至少应该尝尽人生欢乐再走吧。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有可能抗争,不论成败,至少可以尝试抗争,那样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我也许很难有勇气死于某种抗争,但我至少从精神上更欣赏这样的人。
8 ) 逻辑的错
发生在江阳县的这个故事,小媳妇和小银匠之间的孽缘,故事结束之前的所有情节,都是平铺直叙的平淡。
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啦,富裕人家的媳妇偷到了平民人家的公子;或者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偷到了平民人家的闺女;在这个话题上面,“男权中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都积累了蔚为丰富的资源。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银饰》的专利,在千百年前乃至当代社会,白领与蓝领之间的这种男女情事,说好听的叫做追求自由的爱情,说不好听的叫做啥,不说也罢,总之,作为客观存在于这个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类似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值得希奇的地方。
但是,《银饰》在结尾的地方,给人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小媳妇的结局,实在出人料想。
关于小银匠的死,老银匠作过非常仔细的逻辑推理。
老银匠本来不喜欢小媳妇,后来由于小银匠的缘故,老银匠从爱屋及乌到真正接纳小媳妇,已经完成了思想和感情的转变。
但是最终导致老银匠杀死小媳妇的原因,却是一个我们常用的逻辑推理。
一般认为,犯罪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犯罪动机,二是犯罪时间。
在老银匠眼中,小媳妇具备全部的犯罪条件。
首先是犯罪动机,在片子开头,小媳妇委托小银匠买砒霜,就暗示着某种犯罪动机,尽管“这动机”非“那动机”,毕竟也算是一种动机。
再就是犯罪时间,小银匠吃的那泡过砒霜的人参,是小媳妇亲自送来的。
这两个因素搅和在一起,任凭你是老银匠,也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小媳妇就是杀害小银匠的真凶。
在警匪片中,或者在平时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这种推理逻辑,始终被我们坚定地使用着。
但是,事实上这种逻辑可能有问题,至少在《银饰》中就出现了推论错误。
老银匠杀死小媳妇,在他的内心里,也许始终认为是为儿子报了仇。
特别是小媳妇死前说它怀了小银匠的孩子,这更加导致老银匠认为,小银匠的死,是小媳妇在借种生子之后的杀人灭口。
越是这样,越增加了《银饰》的悲剧色彩。
从普通人的逻辑推理习惯来说,老银匠的推理是没错的。
但是,老银匠的推理没错,那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呢?
想不出来,只能说,可能是“逻辑”出了错。
我们所习惯和认同的思维逻辑,所谓的“犯罪动机”加上“犯罪时间”的思维逻辑,肯定有问题。
《银饰》中揭示的这个话题,远远比警匪片所揭示的某种道理,更加深刻。
它至少说明,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逻辑也有错。
正如在电子计算机时代,我们经常面临着“程序出错”这样的问题。
人是好人,如果说有错,那是逻辑的错。
9 ) 没看出主旨~~
看完之后,我在想这部禁片到底禁在哪里。
另外,到底是批判或同情小银匠和少奶奶的爱情,还是唏嘘少爷的同姓恋情结,不知所以然
10 ) 太不像话的性描写
故事结构不比《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差,可惜拍得太得过且过。
作为一部禁片,性描写能不能再积极一些?
小树林偷情拍得太不像话了。
不过女主角漂亮得很古典,可以给两颗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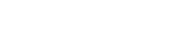
故事完整细腻曲折离奇。每个角色,可怜又可悲。小银匠单纯善良,小媳妇软弱孤独,少爷畸恋自私,老爷强势狠毒,老银匠悲苦愤怒。旧社会戕害人性,文明社会应更多包容性。
情节应该蛮精彩的,就是演得吧,糟心。奉劝女主角,就算不看AV,至少看看三级片嘛,看那叫床演的。
就不可以再烂一点了。。。
这么好的片子这么低的分不科学啊!我觉得这片子是我看过的有龙标的表现跨性别的唯一片子啊!王同辉演的那个角色应该是跨性别了。记得他在最后自杀时旁边的那块布上写着:“宁死不做明德家的人……”不要粉饰的太平,要真实的欲望与人性……明德家的最缺德了,哈哈。
以前中央六看的,我的脚丫疼也总冰冰凉呢,快来个胳肢窝给我
对少爷的异装癖印象深刻!然而我忘了后面的剧情,也记得他老婆出轨…突然发现导演还导了《大鸿米店》,可以可以!
时代悲剧啊 变性人以为吃药能好 碧兰很漂亮啊
这其实是一个时代悲剧。一位县太爷大少爷却偏偏是同性恋,妻子守寡玩偷情小银匠却被县太爷设计害死,最终一尸两命,小银匠父亲也自杀。用同性恋来揭开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对人的毒害,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同时也揭开了过去同性恋的一角。孟瑶也奉献了极大的牺牲,那个年代的电影还是挺敢演的。
女主角真得很不错!电影马马虎虎,题材并没有什么突破!
只记得女主好美,勾引小银匠结果还害死了人家破人亡。
用姜文的话说,挺带劲
胸很正,19,40,1:35:00。
故事剧情太孱弱了…男主最后将死那段总觉得耻度报表。。。
小银匠除了嫩还有啥?
制作糙了点儿,男猪挫了点儿。基本看不下去。
又浪费一部小说
没意思
老黄这部片子,纯属YY无聊,那个小银匠贼头贼脑,严顺开神经质样子,可惜了蜀地风土。
看的时候惊叹于女主的神级颜和身材又觉得眼熟 原来是孟瑶....
总感觉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