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舟记》剧情介绍
玄武书房拟定出版一部面向当代人的中型国语辞典《大渡海》,阅历颇丰且行事一丝不苟的国语学者松本朋佑(加藤刚 饰)作为监修主持工作,谁知他最为器重的编辑荒木公平(小林薰 饰)却到了退休的年龄,选择回家照顾病中的妻子。此时编辑部中仅有做事浮躁的西冈正志(小田切让 饰)和临时工佐佐木熏(伊佐山博子 饰)。荒木和西冈多方物色,终于相中了营业部内不善于和人交往却对词语有着敏锐认知度以及做事极为认真投入的青年马缔光也(松田龙平 饰)。浩瀚的词语海洋,马缔与同事们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编制一艘驶向彼岸的小船。他们甘于寂寞,却也收获着弥足珍贵的幸福…… 本片根据三浦紫苑的同名原作改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王的盛宴Okura~难解事件搜查~芝加哥警署第八季高岭之花周末狂飙绿色的声音双生爱相杀一手托两家生死围城老吴的账单9号秘事第七季影王少帅的初恋格莫拉第二季末世殖民地生死林地大脚怪:内心的怪物言语如苏打般涌现无处安放冬年糟糠之妻俱乐部我的罗曼蒂克香肠老爸绝色逃生死亡夜线凤囚凰太空狗与涡轮猫墓客迷踪贷款买下了男朋友夺金四贱客失踪
《编舟记》长篇影评
1 ) 母亲不是天然的
虽然母亲是自然赋予的角色,但没有一个母亲是天然的母亲。
看完后我主要想说的是…为母则刚,希望承担母亲的责任,享受孩儿伏在膝上的温暖也好; 不舍自由,热爱独处,害怕麻烦也罢。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误。
需要避免的是“违心”和“善变”…女人要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不要心中向往自由却又早早生下孩子,财力不佳却意外诞子,这是违背人心的。
如此,你不会快乐,孩子或许也不会快乐。
就像片中主人公一样不舍的追逐梦想 时刻觉得孩子是累赘……也不要过于善变,一会想要抛弃孩子,一会又想念他们…时机总是不对 错过的时光也不会倒回 你永远在后悔。
2 ) 感觉女主其实是死了,几个影射的猜测
女主把娃娃拿走影射自己年轻时的离家出走,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爱。
帮助娃娃把脏水吐出甚至吐出一条虫是在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妮娜刺她代表她的女儿们并没有原谅她,而是很恨她。
出车祸后到海边其实是幻想,幻想女儿们原谅了她,电话里有说有笑。
女主也并不是只离开了女儿们三年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回去。
因为女主回忆里面完全没有女儿们长大的影像,都只是她的口头表述而已,也仅限于女儿们现在的年龄。
她不小心触碰到手机大女儿Bianca的号码,拨出去接通的确实妮娜。
说明她根本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是潜意识把妮娜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其实女主可能患了脑癌,开车时候发作出车祸了。
因为在玩具店里怀孕的女人诅咒谁拿走了娃娃谁就得脑癌,这是个暗示。
而女主经常很快起身就会头晕,也预示着她有隐疾。
继续讨论Lost Daughter里面教授和女主偷情的这段。
很明显教授和女主是精神上先互相吸引的,然后教授采取主动想和女主上床的时候为什么会和女主说,因为你有家庭所以要你主动,结果再滚床单?
因为此处教授代表的还是男权社会,他欣赏女主作为唯一的杰出女性在他们的学术圈,他希望和女主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立场是希望女主是不守妇道的,因为他要享受这个不守妇道的成果和甜头。
然而,在后面几次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对女主表示女主应该要顾及家庭,因为这个时候他作为男权世界的一份子觉得女人就应该守妇道,应该在出轨的同时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是女人的职责。
是不是很双标?
男权世界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这么残酷。
女人是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因为男人主宰这个世界,为了更好的主宰这个世界,男人必须让女人屈服,肉体上的征服加上思想上的统治,才能让男人占尽好处。
虽然教授看上去是女主老公的对立面,但是从男权的角度,他们明明就站到了一起,才显得女主更加悲哀。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有想和女主真正有将来的打算,所以他和她偷情的前提是不拆散她的家庭,这个听上去非常道貌岸然,潜台词其实是,你要抛弃你的家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不背这个锅。
所以女主最后离开了家庭仍没有和教授在一起,这个结果太正常了,换我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因为你而离婚,但不是为你离婚,聪明的男人也应该明白其中的区别。
3 ) 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
没看过原著小说,但感觉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电影,难度在于要以什么来支撑这么弱的一个故事。
开头即结尾,48岁患有脑癌的女教师来到一片谈不上怡人的海滩度假,她观察游客,帮忙找孩子、偷玩偶,与不礼貌的一家人发生小摩擦……若把这些作为故事的主体肯定是不行,即便加上女二号与虚伪男教授的戏、妮娜出轨的戏、女主逃离家庭责任的爽与悔(暗线)、女主与房东的暧昧……也还是弱。
但贯穿始末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吊人,而这种气氛就是女主在最后时光的心理,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故事的间隙。
女主的结局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无情:你若强行挣脱家庭对你的束缚去追求自由人生,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此外,尽管女二与教授的那场戏意在隐喻女主离家出走前的处境,但毕竟完全脱离了女主的内视角而又无处可借,处理得不够专业。
总体还比较喜欢。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4 ) 道德的捆绑是否正确呢?
嗯 看的过程中思考了许多 也带入了自己的童年。
印象中我的母亲也并非真的那么欢喜我 隐约记得孩童时代她对于我的"厌恶"。
(可能出于我自身的不懂事也可能来源吃醋父亲对孩子的爱意高过妻子这一身份又或是她自身保留的孩子气。
)-我也记得那一年和母亲二人去海边 她在沙滩上戏水时的模样 没有拘束 那般自在无虑。
那一刻她或许脱离了一切身份的枷锁 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当下。
我也记得童年时期家庭不算美好的充满争执的氛围。
父亲的缺席及偶尔出现的疼爱。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期待着父亲今晚是否回家用餐。
比起亲自打电话咨询问题的答案 她更乐于把话筒递给我和姐姐。
或许 她觉得来自孩子的问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同意的回复。
-话题扯远了。
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女性作为个体及母亲这一身份间的来回纠葛 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友好方面 以及关于人性的复杂多面性。
开篇 影片中的母亲作为教授这一身份来度假。
她敢于拒绝别人的请求 即便这不过是小事一桩。
不过也正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有自己想法和个性之人 这与之她年少时逃离家庭相呼应。
她在沙滩上观察着另一个家庭 另一对母女。
不时地牵扯出她过往的回忆。
丈夫在家庭中的不作为/孩子们的吵闹/那个丢出窗外而支离破碎的娃娃......很难去评判孩童的行为 无知无畏又有些"残暴"。
但又如父母亲的抉择 同样觉得孩子是一件包袱 阻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婚姻出轨又是否是逃离家庭枷锁的一剂良药?
很难去评判道德问题 当今社会从一而终的又有多少呢?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又是否等同呢?
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果盘/那个被偷走的娃娃 表面看着如此平静而美好 但内里却如此破败不堪。
这是否隐喻这个影片/这些人/这世上的所有家庭/这整个世界呢?
电影院内咆哮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女性的发声永远不如男性的一句怒吼。
那根固定草帽的发簪最后成为了刺伤自己的武器。
前一秒还因寻回孩子结交为朋友 下一秒却被偷娃娃行为所激怒而暴力待人。
这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善恶评判标准 大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去行事。
片中的母亲最终拨通了孩子的电话 又想起了过往削水果皮时的场景。
这算是过往云烟后的醒悟吗?
这便是最后的结局吗?
或许还会流浪 继续新的旅程 但谁又知道呢?
人啊 终究是复杂的。
5 ) 绝望+恐怖
1.大概前半个小时,可以被影片的气氛蛊惑,也可能是刚看完《我能说》的原因?
对比之下觉得镜头语言充满想象力、丰富极了;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疲倦,开始尝试寻找故事和逻辑,来抵抗单调。
2.观影过程中心里是紧绷的,数次默默感慨:这是个悬疑片么!
不过放映完毕,想法变成了这似乎是个恐怖片——一个一旦经历生育,便永远无法摆脱噩梦的恐怖片。
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离开,可以弥补“做自己”的空白、实现理想、看似潇洒,然而却会在48岁的年纪依然被愧疚折磨得体无完肤。
爱=压抑=无法摆脱。
3.更深的恐怖在于,影片的设定中,没有把Leda的痛苦处理成“只要我能想得开,都不是问题”这种个体悲剧,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从泥潭中拼命爬出来”的出身,用一个名叫Mina的洋娃娃串起她的前半生:Leda自己,是第一个Lost Daughter,母爱的缺失确确实实给她造成了无法弥合的成长伤痕,所以她无法心安理得地用一种潇洒的、现代的价值观来安慰自己、来装饰自己从女儿处出走的行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个中感受。
于是悲剧拥有了必然性,变得恐怖。
4.也许我可以去刷一刷《坡道上的家了》!
6 ) 拿走娃娃
在看原著和电影时,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Leda拿走了娃娃。
在书中,有一处电影没有的展现的Leda的心理描写,发生于这一行为之前。
“Or the voices, yes, especially the voices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ibuted to the doll. Now they gave her words in turn, now together, superimposing the adult’s fake-child voice and the child’s fake-adult voice…But no, I felt an unease as if faced with a thing done badly, as if a part of me were insisting, absurdly, that they should make up their minds, give the doll a stable, constant voice, either that of the mother or that of the daughter, and stop pretending that they were the same.”吸引Leda目光的母(Nina)女(Elena)对着娃娃说话,母亲的孩童声音和孩子的成人化声音都被附加于娃娃身上,这种不和谐使得Leda不安,她认为并在心里坚持娃娃应当拥有一种同一的声音。
为什么娃娃拥有同一的声音如此重要,以及娃娃是什么?
在海滩上,大的威胁来自于电影中得到强化的男性帮派的粗俗,暴力,和凝视。
而直击内心的是这种暴力也复制于母女关系中。
混杂的、互相模仿的女性声音失去了边界,女孩将成长为没有出路的年轻母亲,一具性凝视下的身体,而年轻的母亲孩童般的声线则显示其当下险恶处境及早熟的母职扮演之荒谬。
她们在男性掌控的粗俗世界中的关系是权力的争夺关系,一种病态的相互折磨。
强加于娃娃的声线是将这种母女关系具象化。
借由这一纽带,Leda不仅回忆起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而且因这一不和谐的破绽重温了对于划分明晰的母女权力级别及身份的维持的失败。
她所想要维持的有文化,有身份,有学识,从容镇定,独立的姿态,以及女儿成人离家后因获单身自由而重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都在这一不和谐破绽下被瓦解。
女儿不会成长为成熟独立的女性,母亲也不会得到解放和出路,一切并不是随着岁月向前而正向前进式地发展。
正如书中Leda的顿悟,“ a mother is only a daughter who plays.” 她以为已放下或逃离的处境重新回归。
一具身体可以拥有两种声音,正如作为女儿,自我,和母亲的界限并不明晰。
Leda又一次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而是某种母职功能存在。
这种功能的失败蔓延至定义其整体。
一切社会阶层攀爬的努力和文明的表象不堪一击,从稍稍破绽就可瞥见一切仍是由暴力和无理性笼罩的深渊。
Leda的边界感受到了威胁,与远远逃离的低阶层家庭背景和残酷世界中失势状态的曾经溶解在一起。
拿走娃娃的缘由因此是多层次的。
首先,这是她针对男性恶意所带来边界感消失的反击。
Leda本是来到海滩悠闲度假。
Nina和Elena所属的男性主导的大家庭却粗鲁地侵入了静谧的海滩。
在书中,他们操持的地方口音刺激着Leda的神经,使她联想到那不勒斯郊区的暴力和粗鄙,以及其与母亲失败的关系,这是她毕生致力于逃离和划清界限的地带。
电影中,英文的共同操持使得方言的象征削弱,但仍有痕迹,而这种粗鄙的暴力更多由行为展现。
初始,男人们开着快艇,快艇锋利地划破平静的水面和其象征的平静。
渐进,群体中的女人和孩童在男人对所有物的宽容和’庇护’下对其他人进行指使和羞辱,这种矛盾在电影院中上升到顶峰,Leda的反击呈现十足无助。
拿走娃娃,是剥夺这一群体所庇护的脆弱所有物之最脆弱成员,造成的动荡遍及整个群体,是一种复仇。
其次,拿走娃娃也是一种惩罚和重赋权。
惩罚女儿,也惩罚曾作为年轻母亲的自己。
在Leda的回忆中,孩子并不是纯洁的,而是近乎于邪恶的存在。
会毁坏其Leda幼年珍视的娃娃,对无辜的身体进行摧残和标记,会怀着纯粹又无辜的恶意打她,会拖累她的学术生涯,使她失去自我,失去身体的魅力,使她再次陷入无法挣脱出身之困境的热潮。
在海滩上她被年轻的母亲Nina吸引,是在其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无助的身影。
在其凝视下,这具身体极富魅力。
电影中,在Leda与其的短暂社交中,这具身体拥有着强烈的同性吸引力。
然而这具身体的行动随时由其女儿的需求所定义,又被其所处的男性大家长家庭所限制,呈现无助之姿。
沙滩是其失败展演和发挥魅力的有限舞台。
另一方面,Nina与Leda的女儿年纪相仿,她透过其姿态也对叛逆敌对女儿作关联。
因此,可以说Leda从沙滩的母女看到了女儿的幼年和成年两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将母亲看作母亲这一身份。
Nina占据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如同娃娃(Nani与Nina的字母位移和对照)。
拿走娃娃,是重访Leda与女儿的旧时关系,并重新通过剥夺玩具的形式幻想这一关系之主导。
这种破坏性的重赋权也曾以Leda出轨的形式实现过。
在与有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教授Hardy的外遇中,与其说是重拾激情和爱的能力,不如说是透过上位者的凝视和这一关系产生汲取上其权力的假象。
获得上位者的认可和爱,进入学术界,远离家庭,远离母职,树立自我的身份和边界成为可能,但这是困难且煎熬的,甚至羞耻的。
现在,只需拿走绑定年轻母女的娃娃并带入年轻母亲身份就可以实现母女关系中的赋权。
女儿的精神支柱被抽离,只得陷入无助与无理性,而年轻母亲虽然心焦于娃娃踪迹不明,却不再需要陪女儿过家家,因为道具之不可寻。
因此年轻母亲拥有了更多精力抒发自我之苦恼,散发年轻的魅力,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与Leda交谈,与Will(文中的Gino)调情。
但同时,Leda曾离开女儿对她来说是煎熬和自责的。
影片中,透过她对Nina的凝视,可见后者之不成熟。
语言粗俗,竖中指,对女儿忍无可忍的脏话,对婚姻关系的背离,浓妆严密,衣着暴露。
拿走娃娃使得Elena高烧不退,Nina的生活更为焦头烂额。
Leda借此对Nina母职的过失进行惩罚,但同时也是对其自身在与女儿关系中的不称职进行惩罚。
再者,借由对于他人关系的操纵,使得Leda获得了一种去性别的赋权。
她旁观一切,却掌握了事件的核心,这种感受是平常生活中需掩饰和不可得的。
最后,拿走娃娃是解放。
在电影和书中都有一场景,及Leda在偷走的娃娃口中先是发现了脏水,而后又在清洗过程中发现了蠕虫。
天真无辜的娃娃口中爬出蠕虫,如同片中和书中Leda屋内的一盘被赠送的美丽如静物画的水果,表面魅力无暇,内在已经腐烂。
这可看作平淡体面生活充满肮脏和危机背面的隐喻,也可看作一个体面个体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但蠕虫又不止于此。
蠕虫是一具女性身体的产物,如同婴儿寄生于母体。
Nina和Elena在沙滩上将娃娃作为共同的孩子抚养。
而被赋予性别的娃娃则继承了这一性别和母职,在原书21章Leda与Nina的对话中可知,Elena决定让娃娃同其姑姑Rosaria一样怀孕。
蠕虫则是娃娃孕育的孩子。
被寄生与可惧的寄生正是母体与孩子的关系。
这种敌对及黑暗的关系很多时候成为母女关系的主导,打破理所应当的爱的滤镜。
拿走象征有孕育能力的母体的娃娃并帮助其清楚腹内脏水及蠕虫,也是对Nina和Leda自身从母女关系和母职中进行解放。
在书中,清除蠕虫的篇幅(22章)为:“ I should have noticed right away, as a girl, this soft reddish engorgement that I’m now squeezing with the metal of the tweezers. Accept it for what it is. Poor creature with nothing human about her. Here’s the baby that Lenuccia stuck in the stomach of her doll to play at making it pregnant like Aunt Rosaria’s. I extracted it carefully. It was a worm from the beach, I don’t know what the scientific name is: the ones amateur fishermen find at twilight, digging in the wet sand, as my older cousins did four decades ago, on the beaches between Garigliano and Gaeta. I looked at them then spellbound by my revulsion. They picked up the worm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stuck them on the hooks as bait; when the fish bit, the boys freed them from the iron with an expert gesture and tossed them over their shoulders, leaving them to their death agonies on the dry sand.I held Nani’s pliant lips open with my thumb while I operated carefully with the tweezers. I have a horror of crawling things, but for that clot of humors I felt a naked pity.”由此可见,Leda想到童年时期男孩子们用类似的蠕虫作饵钓鱼,并在此刻摒除对爬行软体动物的恐惧而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同情。
被用作饵的蠕虫此刻使得Lena想到了母亲这一身份下的她和Nina。
她们都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作为一种功能而非独立个体而存在(这书中17章,Leda提到这点“How foolish to think you can tell your children about yourself before they’re at least fifty. To ask to be seen by them as a person and not as a function. To say: I am your history, you begin from me, listen to me, it could be useful to you”)。
拿掉蠕虫,解救的不仅是娃娃,也是蠕虫本身,是解除相互纠缠的关系。
娃娃主导了Leda海滩上诸多事件的推进和发生,也主导了其情绪的变化。
在小说最后,Leda向认为能同她产生共鸣的Nina坦白是自己拿走娃娃并被刺伤并踏上归途,也意味着她的痛苦虽说并不是女性和母亲独特的体验,但仍然得不到包括其他女性在内的人的理解。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她仍需独自面对自我的羞耻和苦难。
她逃离被暴力和粗鄙充斥的海滩,如同逃离一个微缩的糟糕世界。
7 ) “永远不会好的”
近期看过最窒息的电影。
孩子如同恶魔一样吞噬、占有、破坏着母亲的一切,站在无法被丢弃的可能上恣意妄为。
没有带着审视批判的想法去看Leda拿走娃娃,就像处于彻底崩溃状态的Nina没能注意到的那句“永远不会好的”;也没有指责父亲的缺席,简直要习惯这些失踪,尤其其家族的人都带了一些不好惹的感觉(不论这部分的强调是客观还是leda从现实的延伸主观臆测),暴躁的情绪和骂人的话对身边的人更不会少,那些让Nina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帮凶。
娃娃被Leda翻来覆去,被涂画(如同Leda曾经的娃娃被她的女儿如此折腾)被隐藏又被擦净归还;开头与结尾和女儿的两通电话并没有明显的情绪区别,她始终在隐藏自己的情绪,只有这个被拿走的娃娃承受着——她品尝破坏的快感与痛感,又在阳光下感受Nina的崩溃,如同照镜子一般看着年轻的自己,被挤压被侵占,于是depressive于是偷情,逃离责任逃离家庭,在新的肉欲与爱欲、背叛与重构间再次膨胀起自己的灵魂。
Leda与Nina,现在的Leda(未来的Nina)与现在的Nina(过去的Leda)如同母女版的岁数差,可现在的Nina无法共情Leda,也无法预料未来的自己,于是将被赠予的温柔善意刺向成熟的腹部(细节是腹部,一方面二人处于坐姿,这是最顺手也最隐蔽的位置;二是崩溃的根源“子宫”所在。
或许是过度解读了)。
处于暗处的是母亲,道德、情绪、规范习惯的暗处——坠入黑暗的边缘,但片名却是lost daughter,身份的交错,是因为暗处的devil是女儿,或是如同宿命一般重演曾经的加害者亦是/也将成为受害者,还是女儿是处于暗处的人安全的避风的渴望的身份和位置?
8 ) 费兰特访谈:玛吉·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译文)
一位母亲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萦绕着埃琳娜·费兰特的所有小说,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它成了压倒性的核心主题。
48岁的比较文学教授勒达·卡鲁索在海边租了一套公寓过暑假,在那里她努力工作,并反思自己与两个女儿的关系。
她有没有辜负她们?
她在乎吗?(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在演员玛吉·吉伦哈尔的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勒达由奥利维娅·科尔曼和杰西·巴克利(在闪回中)饰演,两人共同捕捉到了书中的一些怪异和暴力:母性的粗糙边缘,以及其中残酷和愤怒的时刻。
这是费兰特的第一部英语改编电影,吉伦哈尔的剧本惊人地忠实于原著,结构上更像惊悚片,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导演的选角安排更加不拘一格,其明星阵容还包括达科塔·约翰逊、因《正常人》而崭露头角的保罗·麦斯卡、艾德·哈里斯和彼得·萨斯加德(吉伦哈尔的丈夫)。
要将一本充满隐喻、讲述不可靠叙述者狂热梦想的书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伦哈尔曾说,她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时,她想,这“多么令人兴奋和危险啊”,于是开始给费兰特写一封长信。
人届中年的勒达被在同一海滩度假的一个年轻女人(约翰逊饰)迷住了:一个坏妈妈注视着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宠爱着她的女儿,而女儿宠爱着她的洋娃娃。
小女孩短暂失踪后,勒达偷走了洋娃娃,给它买了新衣服,从它嘴里抽出一肚子海水和一条虫子。
洋娃娃是费兰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堕落的孩子,失踪的女儿。
这本书只有140页,具有费兰特后期作品中较少出现的清晰和克制的特点。
它也可以很有趣,吉伦哈尔和科尔曼倾向于这样做。
勒达屈服于她最离经叛道的冲动: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欺骗了她的丈夫,偷了一个孩子的东西。
但她并不后悔。
“多可怕啊,这是为什么?”当勒达说她离开了她的女儿们时,一个女人问道。
她回答说:“我很累。
”吉伦哈尔在2018年获得了改编权,费兰特当时表示,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
”她补充说,她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
所以我开始问她和吉伦哈尔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暗处的女儿》2018年,你写道“玛吉·吉伦哈尔是我喜爱的演员”。
你对她的作品了解多少,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埃琳娜·费兰特:在电影《秘书》之后,我想我几乎看了她在意大利上映的所有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
玛吉·吉伦哈尔很棒,她有一种独特的美,在银幕上的表现充满了智慧的能量。
当我得知她对《暗处的女儿》感兴趣时,我立刻认为她会做得很好。
我对此很确信,读了她的剧本后,我给她唯一的建议就是不要让自己被类型片(危机中的情侣、惊悚片、恐怖片)的规则所束缚,要坚持一种“略微狡猾的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的来往太少了,不足以开始一段更复杂的关系,即使只是书信来往。
你还写道,吉伦哈尔可以自由地把《暗处的女儿》拍成她自己的——“即使她只是想把它当作自己创作冲动的跳板”。
她有多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她的创造性如何?埃琳娜·费兰特:我通常避免根据电影对书的忠实度来称赞它。
一部好的小说是难以捉摸的,作为电影制作人,你不可能真正拥有它,你只是对它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当然,这丝毫不能证明那些电影制作者是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把一本书想拍成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
草率地低估小说的策略往往会导致混乱,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叙事方面。
那么,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部根据好书改编的好电影?
它捕捉到了写作的每一个冲动,并找到了方法将其转化为影像。
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忠实,而是创造,而且往往是背叛。
我们的目标是抓住这本书的核心,或者至少是编剧和导演对它形成的想法。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最不忠实的电影可能会神秘地接近原著。
吉伦哈尔就是这样。
她的电影看起来非常接近小说,正是因为它对背叛忠贞不渝:这是最有成效、最令人惊叹、最难以做到的一种忠诚,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你最喜欢这部电影的哪一点?
在这个你自己的故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给你不一样的印象?埃琳娜·费兰特:说实话,我喜欢整部电影。
吉伦哈尔拍出了真正的电影:她相信影像;没有画外音来帮助故事发展;对话是暗示性的;手势饱含感情,即使只是暗示;过去在此刻的闪现是令人信服的;一些小事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氛围。
而且,她能将书中意象转化为有着自己风格的影像,这一点非常奇妙:闪烁的灯塔光束、一碗美丽却已经腐烂的水果、枕头上的蝉、削成蛇形的橙子皮、藏在洋娃娃肚子里的虫子,等等。
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模棱两可的,揭开又藏起来,藏起来又揭开。
因此故事流畅,却又沉入其黑暗面,在内部挖掘。
是的,这是项了不起的工作。
片中有一个时刻——确切地说,有两个时刻——在我看来有一种罕见的强度。
在第一个时刻,年轻的勒达——杰西·巴克利饰演,我们不应该错过她的表情——向她困惑、惊慌的情人承认,她和女儿们的电话让她厌烦,也让她们厌烦。
第二个时刻,也是最可怕的时刻,由无与伦比的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勒达,控制不住地哭泣着承认,当她离开孩子们时,她真的感觉很好。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在银幕上,它以一种令人痛苦的力量冲击着我。
你说过这部小说比你的其他小说更冒险——你是在“没有救生衣的情况下冒险进入危险的水域”。
为什么这么说?
你重读过它吗?埃琳娜·费兰特:没有,自2006年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后,我就没有重读过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稿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
但从2003年开始,我重写了很多次,我似乎不知道如何结束它。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个女人如何在巨大的痛苦中放弃自己的孩子,感到的不是内疚,却是轻松、全然的快乐。
我想描述那种喜悦感并没有消失,即使这个女人回到家,被她自己的矛盾打败,并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但荒谬的是,作为叙述者,我自己却感到内疚。
我很不安,因为我在钻研那些素材,但我越想停下来,就越高兴地继续钻研下去。
这本书是以意大利南部为背景,而电影是在希腊拍摄的,由美国人执导,英国人主演,还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
你觉得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得失吗?埃琳娜·费兰特:我刚提到的背叛就包括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
有些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它们可能导致叙述机制的严重简化,更糟糕的是,导致角色缺乏可信性,但这并没有发生。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有一种力量,与地点变化以及“意大利风情”和“南方风情”的丧失截然不同。
你怎么看待奥利维娅·科尔曼对勒达·卡鲁索的诠释?埃琳娜·费兰特:你知道,当你写作的时候,人物的身体特征是确定的,但又是可变的。
词语可以界定某个东西,但也会使之模糊不清,这就是每个读者都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私人书籍的原因之一,甚至作者心中也有一个与出版版本仅有少部分重合的文本。
一旦把它拍成电影,事情就明显变得复杂起来。
电影是用身体制作的,而这些身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确界定。
另一方面,写作和阅读则跳过一些内容,明确另一些内容,并为不确定的内容留出广阔的空间。
吉伦哈尔打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想的是:她本人演勒达会非常合适。
后来我得知饰演勒达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奥利维亚·科尔曼,我高兴极了,于是我逐渐摆脱了对吉伦哈尔版勒达的想像,谨慎地靠近科尔曼版勒达。
我时不时把它当做一项试验,等待电影的上映。
今天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科尔曼是这个用影像讲述的故事的真正力量。
如果说闪回部分是如此自然地流动,这不仅因为巴克利很出色,也因为科尔曼赋予了勒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想法、感觉或记忆不会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手势上闪烁,哪怕只有一瞬间。
是的,她是一个非凡的勒达。
还有没有其他表演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让你感到惊讶的?
埃琳娜·费兰特:杰西·巴克利,她和科尔曼融为一体,跟两个孩子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刻——更不用说非常艰难的时刻了。
但说真的,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满意。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娅·科尔曼在勒达给尼娜别针的那场戏中尤其感人。
你有没有和别人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过你的作品?
你有没有过冲动,想要公开说:“那是我的作品!
”就像你的某个角色可能会违背他们更好的判断那样?埃琳娜·费兰特:这种经历反复出现过。
第一次发生在25年前,当时我看了马里奥·马托内(Mario Martone)根据我的小说《讨厌的爱》改编的电影。
看到它极其感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界——我非常高兴,并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喜欢这点,即这部电影源于我的作品,我经常向朋友和家人夸耀它。
但仅此而已。
《讨厌的爱》海报电影《暗处的女儿》与小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闪回中勒达的母亲缺席了,艰难的母女关系也没有出现。
你觉得遗憾吗?埃琳娜·费兰特:在吉伦哈尔选择的含蓄节制风格中,对母亲有短暂提及,还有母亲送给勒达的洋娃娃,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
然而,我的确为这些缺失感到遗憾:勒达两次怀孕的差别,一次容易,一次困难;重点是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还有那个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完美妈妈的家族友人,羞辱了勒达;以及我故事结尾那句简短的话:“我死了,但我很好。
”不过,这部电影已经时长两个小时了,而且它本身就很好。
母性的黑暗、暴力背景仍然有力地浮现出现。
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失踪的洋娃娃展开,这也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埃琳娜·费兰特:我想我玩娃娃玩得太久了。
甚至到了13岁左右,我还总是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很难与它们分开。
它们的象征意义是复杂的,可能在我写作时也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但在我的故事里,娃娃确实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是玩具,而是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有时是我的母亲,全都沦落到服从我的地步。
Netflix也在改编你的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将在那不勒斯拍成八集连续剧。
你会参与吗?
埃琳娜·费兰特:我的角色是阅读剧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会介入。
对几乎所有由我的书改编的电影作品,我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很费心费力的。
有时我对别人的作品很满意,有时我想自己从头写到尾,再重写。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看守我的小说,我自己也经常提出书中没有的场景。
事实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创造。
我不能接受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我的文本被颠倒过来,因此我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影视化的版本能否取得成功。
总的来说,我的建议是一丝不苟、非常坦率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我缺乏安全感。
参与剧本不是我的工作,我同意做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也因为我一直对电影充满热情。
我很快就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把你的期望建立在剧本上是有风险的,你必须等着看电影。
看初次剪辑版的那一刻是我最害怕的,是我最沮丧的时候,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在合作剧本时是个大麻烦,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个观众着迷,我就会被迷住,我对缺点是宽容的。
迄今为止,与我合作过的导演都知道这一点:马里奥·马托内、萨维里奥·科斯坦佐、爱丽丝·洛瓦赫、丹尼尔·卢切蒂。
我最喜爱的时刻——可惜很少——是电影将书籍从我心中抹去的时刻,那一刻我成为了观众,被银幕上的画面所吸引,爱上了电影,就像我一生中所不断经历的那样。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的文章“True cinema trusts in images: Elena Ferrante on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发表于公众号“界面文化”。
原文链接: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21/12/true-cinema-trusts-in-images-elena-ferrante-on-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
9 ) 四星支持,虽然有点故弄玄虚
短评写不下,移步过来唠叨两句。
整体还可以,让我想起看《坡道上的家》的感觉。
育儿的窒息感,个体自我和母亲角色的冲撞,刻画的很好。
但我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影片有这么两点很不科学:1. 用小年轻提醒女主妮娜一家是坏人的对话,刻意对观众设陷,从而营造紧张压抑的氛围。
这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害我全程都在担心女主偷娃娃被发现,然后遭受攻击,变成悬疑犯罪片。
直到快看完我才意识到,那家人几次可怕的目光,不过是女主视角,是她内心心虚紧张的投射。
啥啊,玩我呢?
本来可以把女主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丰富深刻,加了这句铺垫后反而让片子显得稚嫩不真诚。
2. 女主强烈情绪的底层逻辑令我费解。
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如果如开头表现的那样,女主和女儿仍旧保持联系且关系亲密(毕竟烫了个头发都要跟她聊),就算愧疚一直压在心底,也不至于还这么沉重别扭吧,乃至动不动就湿了眼。
如果她果真失去了其中一个女儿(未可知),她的情绪也应该是妮娜找孩子的时候才爆发(勾起丢孩子的回忆),而不是一开始看到小孩一家就很不自在很难受。
也是有些刻意营造了。
以上种种,看完回味一下,感觉整部片有好几处都给我故弄玄虚的体验。
当然,都说了我是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希望可以蹲到一个科学的解释。
10 ) 打call要打在奥斯卡之前
三年缺席,一生负罪的母亲借刀向自己复仇,不死一回到天涯海角都找不到peace and quiet;抛妻弃子的男人们却一辈子坦然潇洒倜傥放浪形骸,会煎条鱿鱼就能自觉是个暖男,心中还惦记着自己教会了两个孩子游泳。
“我真是个好父亲”,他们说。
正如Craig Mason说的,吉伦哈尔家的孩子可不用咱们操心了,姐弟俩都厉害。
这是今年我心目中的最佳改编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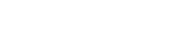























窒息
科尔曼演技了得,把妈妈的内心演活演出来而又不流于表面。作为一名妈妈对孩子有期盼,又有无尽的悔之晚矣,后悔没能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我看完觉得跟《驾驶我的车》正好对应,一个西方一个东方,一个女性一个男性,一个文学一个戏剧,最后都跟自己和解。话说终于在片里认出了一堆熟人,还有女主的几件浴衣好看的。
想象公路上的热浪,透过它看世界,一切都会随之晃动变形。片中,被抛弃的女儿就是莱达的“热浪”。内疚是可怕的,它无时不刻地折磨着你,吞噬着你,无处可逃,无法弥补,可回到当年的绝望处境,选择很可能还是同样的。
恐育阵营又新添一个力作!
厌倦了这种费兰特式的重复,而且影像也是稀碎,没什么意思。
有点想法,这样一个逆反的母亲形象令人信服,对传统道德观的挑逗十分成功。但这情节还是太单薄、太容易预测了。前半小时让人以为女主只是因为愧疚而心神不宁,在捡到娃娃不还后才多了一层悬念,但如果说闪回的情节是清晰展现、价值取向明显的话,那现时的情节则是过于发散的(与莱尔、威尔、卡莉的互动算什么?独处时的受惊与觉察到的异样算什么?不一定都与其心理有关)。如果任何事情都用神经质来解释,那么至少也不够多变化和层次。
演得不错。其他的请参考评分。
C-. 简单的故事,幽微的情感,却完成得捉襟见肘而一地鸡毛。科尔曼游荡,科尔曼崩溃,科尔曼回忆,再用看似压迫实际毫无情感意义的特写镜头串起来,就成了本片。希望导演们能明白,表达微妙复杂的情绪,不是要全程怼着脸才能拍的。
真实深刻,细思极恐。以女性的视角探讨女性的困境与枷锁,透过度假沙滩的所闻所见引出潜藏内心深处的酸楚与苦闷。妮娜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都是过去的自己。当坠入回忆的漩涡,流露出失控的情绪与状态,才将女性作为母亲这一天职的挣扎赤裸展露。伟大与辛劳的背后是放弃自我备受育儿煎熬琐事折磨的抉择,其实这种略显畸形的社会理念是对女性的不公挫伤与道德绑架,母亲的职责让她们无从选择,只能甘愿牺牲与接受惩罚。故事的女主因为缺失的陪伴始终活在自责的懊悔中,劝诫别人也在解救自己,可一切都悬而未决依旧破碎,罪恶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残忍……
恕我不能理解其中深意,并且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就感觉年轻的Lela很有味道,年老的Lela总有点我不喜欢的味道,就像我也不喜欢她演的女王。
nyff看完Q&A才发现Jake Gyllenhaal带着小女友坐我后面🤭!!圆满了
两个女主都很好,而且她们真的蛮神似的。(已经完全忘了小说讲了啥但是有被trigger到……
飞机上看的,好像和原著有出入,落地从晴天步入阴霾似乎正好对应了结局。在电影院大吵大闹的人真该死。
作为生活中只担任过女儿角色的我,来看这部电影,那种对爱的回应的渴求无果,强迫症般,多么熟悉,如此窒息。本想可怜被孩子玩弄的手中的娃娃,却赫然发现她对着娃娃叫妈妈,而这个被蹂躏的娃娃却又被女主偷走尝试修复,一个又一个的连环,一圈套着一圈,这就是作为女性永远也逃脱不了的人生困境。可笑的是,虽然家是所有一切的罪魁祸首,但家依旧是那个落荒而逃的你的避难圣地。
私以为 Maggie Gyllenhaal 的导演首秀表现很好啊 her intellectual ambitions and visions really paid off 把费兰特笔下人物的神经质 角色之间那些奇奇怪怪的 dynamics 还有 boiling female rage 展现得非常好 / 三位女主的表演也都很出色 Jessie Buckley 和 Olivia Coleman 眉眼间竟真的很像 穿豹纹白得发光的达妹太美啦 / Paul mescal in short shorts is delicious *chef kiss* / 就连观影时发放的 screener brochure 设计也非常喜欢
演员当导演的话,优势在于更能与演员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但是劣势在于欠缺一些技法和对于整部电影的掌控,导致电影时常陷于演员的情绪中无法抽离,显得矫揉造作。这部片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剪辑有点问题导致闪回的段落语焉不详、有点莫名其妙,破坏了整体的节奏,看着实在让人泄气。PS,科曼的表演没问题的,不过其他那些小配角就不一样了,大材小用。
4.5 长焦特写拍出的细腻故事,让人几乎触到文本原有的肌理。狭窄的视野和交错的声音还原了那些烦躁又失神的时刻。即使费兰特读得不够多也会发现一些重复要素:知识分子的骄矜,闯入者,社群和个人的对立,秘密,偷情作为不自觉的反抗,女性启蒙者们,对称关系,暗处的缺失。小说改编电影总是留下很多有趣的象征谜题:偷窃是报复还是弥补母爱?玩偶是最完美的“女儿”吗(因为它不主动索取或抗议,又随时乐于接受单向的“爱”)?给出的礼物变成武器,是不是在嘲弄主角的自作多情?观看时暗暗揣测,或许费兰特的故事因为过于诚实所以她必须匿名。尽管对她笔下自我/事业和家庭/社群的对立仍然怀疑,但一代入私人的成长经历,自己对家庭的期待和焦虑,就明白这或许是普遍意义上对女性的尖锐追问
丢失总是双向的,女儿失去了,母亲也就迷失了。忽然意识到以往大多数影视作品对母职体验的描摹都是有意无意想象性的。育儿之苦无非几声哭、一场病,戏份都是要腾出来留给儿童无邪母性无私的。(看看阿莫多瓦那平行母亲,轻轻松松都不妨碍克鲁兹和她的家居继续美丽。)要么就是戏剧性、英雄化的含辛茹苦,回避身为人母的日常经验繁琐堆叠,也就驱逐了普通观众代入的可能。即便有些离经叛道的母亲遗弃家庭,也绝少刻画她还“在职”的前史,而都是“离职”后孩童无辜母亲有愧的后传。你想晒会儿太阳,椅子有人帮你挪。选择了做母亲,当然应对子女负责。但母性阴影后那个曾经完整的自我,她的抑郁疼痛又该何处去说呢。那首好听的theme,名为Let Me Tell You All About It。
平行母亲,生育之痛,两位社会标签定义“不称职”母亲,游离在追求自我和繁琐现实的矛盾挣扎之中。Olivia Colman表演精彩,但整体叙事形不散神散,很难集中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