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未来》剧情介绍
影片通过深圳特区的几个大学生在校园和社会的人生经历以他们所酷爱世界流行的极限运动——滑板作为引线把整个故事情节给有机的串联在一起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作为80后的新生一代对待当今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的认知程度也细腻地反映出作为深圳特区第二代青年移民独特的感知个性、非同寻常的道德理念还有他们不懈追求时代新潮的崭新个性和奋斗精神。 整部影片洋溢着浓郁的青春气息、鲜明的时代特征、前卫的动感品质还有独具特色的南国风情;此外镜头的转换、色彩的运用、不同滑板场景的交叠转换令人在感到异常观感效果的同时也发自内心地倍感清新、时尚、阳光的元素包裹其间。由于该片的编导和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均为80后的新生一代又都是高等艺术院校的专业生再加上充满动感节奏的滑板运动和专场比赛使得整部影片自始至终向人们传递出一种扑面而来、挥抹不去的时尚元素和高强度的运动频率。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生死劫杀1946惊天大逆转五月的声音假面骑士EX-AID建党伟业花与罪被风吹过的夏天而你刚好发光埃达克岛岛海盗宝藏更好的姐妹金山伏魔传红番血路第一季记得你洪水未至神椿市建设中。暗夜情报员第一季神之一手:鬼手篇屠夫道士出山2:伏魔军团扑通!扑通!花少年鬼眼狂刀猫是要抱着的杀戮射击我家的女仆太烦人了!雨中的秋城怪物弹珠THEMOVIE空之彼方户口犯罪都市4山脉公路甜心宅急便
《滑向未来》长篇影评
1 ) 直面女性的困境:痛苦,欲望,悔恨,自我
在众多我看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电影中,这部是我认为最直面女性困境的一部,它的精彩程度故事构架和对女性问题的迎头痛击让我陷入了和电影一样的混乱和思考。
故事里的女性不伟大甚至自私,但我却认为这正是人类的复杂和很多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当我的身份转变,意外的成为了母亲,我要如何抉择自我和母亲的角色?
是否,女性作为一个个体,不可以自私?
故事中不只一对母女,最直接的是女主和她两个女儿尤其是大女儿,她触景生情的妮娜和她的女儿,以及藏起来的女孩和娃娃,即将成为母亲的卡莉和女主与她的母亲。
这些女性的关系的纠缠和延续是故事的主线,穿插进来的是丈夫的失能,意外的心动和他人的凝视。
电影用碎片化的故事,摇摆的镜头,塑造了极为立体的却不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母亲的样貌:她年轻貌美还有未竟的事业,她对事业专注或对自己更专注,对孩子却耐心有限;她有需求有欲望需要释放也会需要爱和刺激;她爱孩子但更爱自己,她会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离开,也会在年迈的时候为此后悔试图挽回……
都说她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也都在说她当妈前是小女孩,但这些似乎都是在一个“妈妈本应伟大无私奉献,她没做好”的前提下劝孩子原谅的逻辑。
所以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成为母亲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吧,可是好像也都在宣传做母亲多开心做妈妈多伟大,却也没人真实的讲述过生活中细碎的崩溃的绝望。
有快乐吗?
当然有,全家一起开心大笑,远行回家抱着孩子亲吻的样子都不是假的,但痛苦也是真的,累积的伤害也是真的。
这部电影在我心里是一种技术上的成功,如此压抑的题材,对母亲形象颠覆性的讨论和探索,对女人立体化的建立,和温柔的颜色画面,摇晃的镜头和特写配合下,像一根箭直接扎进我心里。
我哭不出来,但我也回不过神。
我想我要歌颂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直面人性的复杂,不要以偏概全的为一个人盖棺定论的重要性,也让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的意义。
2 ) “This is my doll.”“No.She’s mine.”——被诅咒的母亲与失落的女儿
一、静谧的、克制的叙事《暗处的女儿》并非借助话语体系来严肃地探讨母职的意义或公然地提出抗议、进行反叛,而是平静地将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母亲的生存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中,现实与回忆两条时间线交替进行叙事:·蓝色调,明亮日光与昏暗暮色交替的现实
·棕色调,幸福与抑郁交错的回忆
触发回忆的契机是海滩上的一对年轻母女,Nina和Elena。
从暗中观望到因一契机与之相识,Leda越来越近距离地观察到她们的生活,也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自己和Nina一般大时的种种相似处境。
影片中有大量充满隐喻意味的镜头:枕头上濒死的蝉,从底部腐烂的果盘,被松果突袭留下的伤口……这都是对于Leda看似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实则暗藏痛楚与荒谬的一种影射。
除此之外,大量的特写和晃动的镜头,放大了人物动荡不安内心的各种情绪。
二、被诅咒的母亲影片中有三位母亲角色:有两个成年女儿的Leda,有一个小女儿的Nina,腹中怀有一女的Callie。
当Nina丢失的女儿Elena被找回时,三人在海滩上交谈,背景音是Elena持续的哭闹声,暗示着三位女人各自的、源自母亲身份的艰难处境。
1.流失的掌控感影片中,年轻的Leda几乎始终呈现出与传统的母亲角色相悖的形象:应对孩子的纠缠时筋疲力竭、无所适从,甚至情绪失控;竭力想要远离孩子,抓住独处的机会;离开家时欣喜溢于言表;出轨时无所顾忌,把孩子抛到脑后……比起母亲,她在两个女儿面前更像是一个年长的孩子。
当Nina问她,离开孩子的感觉怎样,她回答:“It felt amazing”。
观众足以感受到两个年幼的孩子给这位渴望事业、追求自由的女人带来的沉重压力。
Nina与年轻时的Leda极其相似,被迫寸步不离地照顾女儿让她几欲崩溃,终日沉浸在抑郁的状态中无法自拔。
母职所占用的大量时间、消耗的大量情感与精力,使得Leda和Nina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
而短暂的出轨,或许正是她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欲望来寻回掌控感的一种方式。
2.家庭的枷锁不堪重负的Leda选择了离家出走,三年后才回到女儿们身边。
Nina问Leda,既然离开孩子的感觉那么好,为什么又要回去,Leda说:“I’m their mother. I went back ’cause I missed them. I’m a very selfish person.”她把回归家庭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自私”,然而这种自私实际上来源于她对于女儿本能的难以割舍。
血浓于水的连结,使得对于女儿的挂念成为了融入骨血的情感反应,内疚与悔恨的情绪滋长蔓延,促使着她回到孩子身边。
当人们构筑母性神话之时,母性却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降临在女人身上的一种“诅咒”。
波伏娃认为母性是将女人变成奴隶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憎恶孩子剥夺自己的自主性的Leda,也因伴随着生育而来的母性,变成了无法逃离家庭的奴隶。
在片中镜头较少的Callie与Leda交谈时提到“My sister-in-law had hers right away. Took me eight years”,言语中透露出对于Nina的艳羡和无奈。
八年时间终于迎来一个孩子,背后隐藏的家庭对于母性的殷切期望不言自明。
三、“The lost daughter”&the doll展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存状态在我看来不是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影片的名字“the lost daughter”正暗示着这一点。
它可以有多重解读:·走失的女儿——同样在海滩走丢的Bianca和Elena·失落的女儿——失落了女儿身份的Leda(和Nina)影片之所以聚焦母女关系,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描摹女人的双重身份:母亲和女儿。
在作为母亲的同时,Leda和Nina也是母亲的女儿;在作为女儿的同时,Bianca,Martha和Elena也注定会成为母亲。
洋娃娃在本片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
影片中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深刻。
Leda将自己小时候的洋娃娃Mina送给女儿Bianca(或者说是托付给她照顾),却发现Bianca在娃娃身上随意涂鸦,她于是生气了。
“This is my doll. You can't treat her like shit.”“No. She’s mine.”“Yeah, well, she’s ruined.”接着Leda亲手把娃娃扔到楼下摔得粉碎。
粉身碎骨的娃娃这一段颇有些意味深长。
娃娃作为Leda童年的玩伴,在被女儿占有并“破坏之后”落得了粉身碎骨的结局。
这似乎隐喻着成为母亲后要被女儿剥夺一部分的自我,变得不再完整、独立。
换言之,成为母亲意味着要献祭自己曾享受的童年——献,即为子女提供童年,祭,则意味着永恒地结束自己的童年。
洋娃娃的坠落,象征着Leda女儿身份的失落和童年的终结。
洋娃娃同时也暗示着女性注定既是女儿又是母亲的命运。
当Leda发现属于Elena的娃娃躺在自己的包里时,她愣住了。
导演在银幕上隐藏起了之前Leda下意识地拿走娃娃的动作,因此这一画面显得特别荒诞而引人追问——她为什么拿走了这个娃娃?
在我看来,除了对于自己童年的怀旧与回望之外,她潜意识中也把洋娃娃当成了自己曾经抛弃的女儿。
Leda后续的一系列照顾娃娃、把娃娃扔进垃圾桶的割裂的行为,就像是对于年轻时的自我的修正与重演——一方面,她渴望弥补,渴望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另一方面,她的焦虑、恐惧与自我怀疑依然埋伏在体内。
除此之外,洋娃娃也是片中小女孩们的玩具。
女儿年纪尚小时,就要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把洋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而片中的女儿们却展示出了怪异而叛逆的一面——Bianca在娃娃身上涂鸦,Elena会啃娃娃的脸。
这或许也是对一种埋藏在母亲身份中的焦虑与痛楚的映射。
四、母女的决裂片中Leda和Nina的关系颇值得探究。
Leda第一次和Nina搭话时展现出了一个成熟母亲的姿态,她安抚女儿走丢的Nina,并以极高的效率找回了Elena。
因此Nina看Leda的眼神里有一种隐约的向往和仰慕,之后,她也道出了“I wanna be like that lady”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当Leda讲起自己童年时的洋娃娃时,Nina误把娃娃的名字Mina听成了Nina。
我想这样的特意安排,正暗示着Leda和Nina同为母亲、又因年龄和生长时代的不同而形成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
而她们的最后一场交谈,则象征着母女的决裂。
Nina来Leda的住处找她,向她倾吐自己的痛苦,并期望这个她眼中的过来人能够给予她安慰与信心。
而Leda也充满善意地关怀着她。
然而Leda最终道出了娃娃失踪的实情,并坦承“I’m an unnatural mother”。
她本可以交还娃娃而对自己的“失常”行为闭口不言,但她却主动说出了口。
我想,她或许也在隐隐期待自己的这种“不正常”被另一位母亲接纳——也被自己的女儿接纳与原谅。
然而Nina却由震惊到愤怒,对Leda破口大骂。
走之前,她把Leda曾经温柔地给她戴上的帽针刺向了Leda的腹部。
这个年轻的迷惘者与那中年的“失败者”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痛楚,最终却因为理解的缺失而“关系破裂”。
结尾处,Leda在受伤的肚脐附近摸到了一手血,脑海中浮现出和女儿们有关肚脐眼的回忆。
脐带是母女之间的连结,而斩断连结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
除了在电话另一端,Leda的两个女儿的身影从未在片中出现,Nina的背叛是否暗示着Leda自始至终都没有与女儿达成和解呢?
写于2022.3.24晚
3 ) 全景式展现母职惩罚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晰、具体和完整。
你相信吗?
妈妈是可以不爱孩子的,甚至可以讨厌孩子,甚至恨自己的孩子。
不爱也没有关系的。
费兰特三十多年来执着于在写作中探索母女关系,布娃娃的意象在ta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女儿的化身,也凝聚着南泉社会赋予我们的身份。
偷来的塑料娃娃,嘴里流出粘液和蛆。
这幅了娇小美丽但了无生气的躯壳,就像我的女儿,她即将步我的后尘,在家庭——这黑色的粪坑里沉沦——我好不容易才从这里爬出去。
在眼泪干在脸颊上之前离开家。
--抛弃你的孩子们生活,你有什么感觉?
--fucking amazing.偷情的话要用非母语(意大利语)说出来。
她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能由他来主动吻她,他要等她,一个有夫之妇,由她来主动吻遍他全身,引导他进入她,他才不算失德,他才可以放过自己。
Aka 知识分子如何体面地偷情。
费兰特笔下的女性还没能够脱离与男性的关系而存在,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等,我想到杨荔钠导演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已经可以不需要依附于男性给予她们的身份而真正独立存在,杨导那句“我对所有的男性不感兴趣”仿佛仍在耳边。
观看不同时期女性创作者的面向,就足够令人振奋了。
4 ) 碎碎念
希腊海岛上阳光灿烂,但免不了暴雨忽至,同行皆狼狈。
勒达表面上看来是那个年龄段女性的标杆,脸上没有什么岁月的沧桑,杰出的希腊文学翻译家,连店员小伙计都夸赞勒达的容貌。
可是内里,勒达过去对家庭的背叛的阴霾随时爆发,浩浩汤汤,击垮自己。
面对失控的幼儿,勒达和妮娜都爱她们的孩子,只是没有那么喜欢罢了。
社会给女性强加了太多家庭责任,很多女性在家庭里逐渐逐渐丧失自我,多么可怕。
电影好多隐喻,比如女儿的电话,脏兮兮甚至藏了一条虫的娃娃,什么时候开始,电影都喜欢明线暗线交织,隐喻随时渗透了?
昨日下午在房间一个晒得到太阳的角落里独自看完电影,忽觉困倦,迷迷糊糊睡着,醒来时,深蓝的暮色已渐渐苍茫,楼下的灯光打到天花板上,映出一方白色四边形,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感觉自己像是结尾卧倒在夜晚的海滩上的勒达,不同的是,她能很快迎来第二天初升的太阳,而我还要经历一整个长夜。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女权主义者,许多想法只困于脑海,并不想付诸于实践,许多想法真正并不丰满。
人生里面有太多滋味我不敢去尝试,就这么晕晕乎乎地长到了二十多岁,提到家庭与婚姻,责任与使命,更多的是逃避,只是再长几岁,便真的避无可避了。
5 ) 不喜欢这部片的三个理由
理由1:这部电影对主创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观众的。
观众观影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在看什么?
我为什么要看/在乎?
有很多作品在第二个问题上翻车,故事算是讲明白了但让人实在没兴趣看下去。
这部电影就是典型代表。
它可说是一个供主创发挥才能的理想载体(vehicle),导演通过它展示自己会拍,演员通过它展示自己能演,但观众就觉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很多以“探索主人公内心世界”为己任的电影都容易犯这个问题,比如《女人的碎片》《兔子洞》等,表达远远大于共鸣。
理由2:剥离了时代大背景的Elena Ferrante实在苍白。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成功,固然归功于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但居功至伟的还有故事背后的大背景:战后那不勒斯的蹒跚发展,社会浪潮中个人对阶级和发展的焦虑感等。
这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都能产生共鸣和代入感,比如我看四部曲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那不勒斯和90年代的中国城镇非常类似,油然而生亲切感。
当历史背景被淡化后,只剩下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比如本片中Leda的婚外情其实和四部曲中莱农和尼诺的婚外情非常相似,但四部曲中你能深深体会莱农因为婚姻获得阶级跃升而产生的自满和同时想追求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而本片中,就只觉得这位女学者水性杨花。
理由3:两位母亲之间的镜像关系建立不足。
很多时候,导演觉得自己通过各种调度啊剪辑啊讲清楚了,但我没get到,要不是看了网友们的影评,这些微妙的细节就直接被我miss掉了,不知是我不够细腻还是导演太沉浸在自己的表达中呢。
整部影片极度偏向个人表达而很少考虑观众的接收度,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原谅我不买账。
6 ) 一些感受
我看到了一个蹩脚的人的生活,虽然蹩脚,但她的生活确遵从内心。
生活就是一团糟,活着就像是在乱成一锅粥的生活里找自在。
影片看完,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只是默默的盯着电视,心里只有茫然。
不知道是自己没看懂这部电影,还是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种混沌的生活。
影片讲述的两对母女的生活,在现实和回忆中切换,一边是海边的母亲挣扎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另一边是回忆中的自己和女儿相处的时光。
两个母亲都在挣扎,都感受到抑郁,都想逃离。
在这种生活中艰辛地活着,不是易事。
疲惫感和无力感是我看完影片的感受。
所以到底要怎样生活呢。
//太不敏感了,这部电影讲的是女性啊
7 ) “享受你的症状”:《失去的女儿》与归还的自己
在刚刚过去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就有三部与“母亲”有关的电影: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把抱错孩子又相恋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狗血的故事融入到生命的传承和历史伤痛中;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的《正发生》(L'Événement)带着强烈的痛感展示了一个60年代的残酷堕胎故事,最终斩获金狮奖;相比之下,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的《失去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则显得有点普通,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典型妈妈的故事,曾经她和丈夫离婚,三年不见女儿,如今功成名就,也孑然一身。
一直以来,影像中的母亲都被看作是社会征候的显影,因此最被关注的也是其作为社会形象的价值和意义。
但即使只作为符号,“母亲”也不该像唐三藏一样被圈禁在指定范围里。
成为母亲,首先意味着具体的身份冲突,同时,母亲将要遭遇的困境也隐含了结构性的社会观念冲突。
因此,矛盾冲突而不是整合统一,或许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这也是近年来母亲题材内转的方向:做母亲还是不做母亲,这可以是个问题。
《失去的女儿》改编自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的同名小说,尽管对熟悉费兰特作品的观众而言,这样的主题并不让人意外,但吉伦哈尔的改编和执导还是让这个故事更有挑战性,也更出彩。
凭借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吉伦哈尔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8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首作奖,并提名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
主演奥利维娅·科尔曼(Olivia Colman)也在《宠儿》(The Favourite)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但对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非典型故事却又是个挑战。
该片的豆瓣评分为7.5(11348人评分),IMDB评分则仅有6.7(52771人评分),更有趣的是烂番茄网(Rotten Tomatoes)的反馈,专业影评人给出的番茄指数高达94%,而观众给出的爆米花指数则只有48%[1]。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时,主要指的是影评人的标准,对观众而言,这完全不是一部好看的爆米花电影。
在这部影片中,母亲既不是我们熟悉的政治隐喻(伟大的祖国母亲),也不是很好理解的社会身份(为家庭牺牲奉献的母亲),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症状——作为母亲的莱达竟然完全不像母亲。
一大学教授莱达拖着一大箱子书独自前往海滩度假,不喜交际的她享受着这种离群索居的悠闲生活。
可突然到来的大家族却打破了这种宁静,为了聚会他们打算重新规划海滩。
莱达拒绝配合换位置,与之产生摩擦,同时却又被大家庭里的年轻妈妈吸引,妮娜母女总让她想起过去。
故事到这里再起波折,妮娜的女儿埃琳娜走丢,莱达帮忙找回孩子,却又顺手拿走了她的玩偶,失去玩偶的小女孩日夜哭闹。
莱达明知妮娜一家被丢失的玩偶搞得焦头烂额,却始终没有归还。
当她终于把修整之后焕然一新的玩偶还给妮娜时,妮娜怒不可遏,用莱达送的帽针捅了她。
莱达连夜驾车离开,影片的结尾又回到了片头,身着白衣的莱达倒在海滩上。
次日清晨,她醒来,在海边一边削橘子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似真似幻中,影片结束。
影片中,莱达的举动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当这些举动和母亲的身份叠加在一起时,就更显奇怪。
假如换成其他人,把玩偶藏起来不过就是让人讨厌的恶作剧而已,但一个母亲这么做,就让观众觉得难以解释——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是不是不正常?
产生这种疑问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影像中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一种清晰的叙事逻辑中。
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改编自高尔基同名小说。
影片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母亲形象,她在苦难中从无知走向革命,用爱和信念接过儿子的旗帜。
这种觉醒也成为20世纪女性启蒙的经典模式,在伤痛中成为革命者。
如果说革命的母亲具有时代限定性,那么我们更熟悉的还是传统的地母形象,大地母亲既是最为古老的女性原型形象之一,也是民间观念对母亲角色的全部期待,她要承受一切,包容一切,让自己成为孕育家庭的养分。
国产影视剧中最有观众缘的母亲通常都是这样的形象。
与无限包容相对的,是《告白》(2010)和《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2010)中忍无可忍绝地反击的“复仇的母亲”,如果法律不能保护自己和孩子,那就亲自来制定惩罚规则。
当一个母亲决定惩罚凶手,她将比凶手更残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仇的母亲”是以另一种牺牲表明了残忍与伟大乃是一体两面。
相比之下,近年国产影视剧中的“剥削的母亲”则彻底宣告了母亲形象的坍塌。
如果说电视剧中的妈妈主要是物质剥削——《欢乐颂》(2016)中的樊胜美妈妈,《都挺好》(2019)里的苏明玉妈妈,《安家》(2020)中的房似锦妈妈——让女儿为家庭造血,越优秀越值得压榨;那么电影中的妈妈则更多体现了情感剥削——《柔情史》(2018)、《再见 南屏晚钟》(2019)、《送我上青云》(2019)、《春潮》(2019)等影片中的妈妈——她们不仅不能再给予家庭力量,反而成了情感包袱和控诉对象。
提出两条粗疏的线索并不是为了论证母亲形象如何具体变化——在这里也不去探讨变化背后的征候性,比如残酷母亲的形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东亚影像中——而是想通过变化来指认形象的结构性:无论如何变化,母亲都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中。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让我们得以准确地理解银幕上的母亲,无论她处在哪一个位面,至少都表明了一点,一个母亲不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而观众也总是通过干了什么来审视她们。
不同的是,莱达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正如费兰特在小说中写到的,“最难谈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2]。
神秘作家费兰特享誉全球的知名度来自于《那不勒斯四部曲》,HBO将其翻拍成了爆红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与女儿们大受欢迎的成长不同,妈妈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关注,也因此,难以被纳入类型化的影像表达中。
在《失去的女儿》之前,费兰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L'amore molesto)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费兰特的笔下,塑造母女关系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强大但却隐身的历史和暴力,在失去母亲之后,女儿才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费兰特想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对母亲的无视,正如她所喜欢的作家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所做的:“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以男性第一人称写作)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实现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死去的母亲、农奇亚蒂娜、同性恋父亲)从包裹里拯救出来……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3]。
把母亲还给自己,这大概是玛吉选择费兰特作品的真正原因。
但电影与小说又截然不同。
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能让读者迅速了解人物内心,但对电影而言,除非借助旁白,否则无法直接转译。
电影更常采用的办法是通过叙事突显因果,通过逻辑理解人物。
正因为如此,吉伦哈尔的改编才显得大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莱达的经历,那么这个人物形象将更清晰,当下的故事或许也会更有张力,但是玛吉没有这么做,她把莱达的故事仅仅限定在海边度假。
两个小时用来讲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太短,但用来讲述一种体验却足够长,在理查德·布罗迪看来,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削减让《失去的女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元电影”:把女性的生命体验还原到微妙的细节和深刻的经历中。
这恰恰是当下电影所缺乏的。
[4]虽然都改编自费兰特的小说,但《失去的女儿》和忠实原著的《讨厌的爱》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不在于取舍了多少,而是取舍本身就是一种重塑。
因为无法把莱达放入既有的形象谱系中,所以我们反复追问,为什么她要把玩偶藏起来,她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女儿?
顺着这样的疑问,叙事的合理性被放到了第一位:莱达可以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观众却必须知道答案,否则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但影片从未解释莱达的行为,这种不解释与其说呼应了费兰特所说的“自己也无法理解”,倒不如说是一种更彻底的回答:把母亲从叙事中拯救出来,面对她的症状。
因此,读解(read)莱达的症状而不是解释(explain)她的行为,就成了观看这部影片的关键。
二要解释莱达的行为,就得把她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再从这个位置出发追问是什么塑造了形象,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
于是,影片中的回忆就成了唯一的线索,我们从中寻找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都凭借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读人物,但这一方式在这里却恰恰构成了障眼法,因为母亲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形象背后有什么,而在于形象本身是什么。
如果说只有当一个母亲服从于母亲叙事,她才能被我们理解,那么莱达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恰恰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没做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母亲的解释其实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背后真正有什么。
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正是为了给母亲带上一张合适的面具,面具能帮我们回避来自母亲的真实面庞——危险的无意识。
钟孟宏的新作《瀑布》(2021)也讲述了一个让人压抑的母亲故事。
正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旦母亲失去面具,生活将变得如何不可理解,如何恐怖。
疫情之下,女儿和妈妈轮流成为病人,只不过女儿被隔离的是身体,妈妈被隔离的是精神。
自从患上思觉失调症,妈妈就成了家庭的恐怖之源,幻想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瀑布”既是妈妈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象征着母女关系的张力和涌动。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母女争吵场景里,灯下的女儿和暗处的妈妈形成鲜明对比,一如失衡的母女关系,摘下面具女儿可以释放,妈妈则只能崩溃。
妈妈生病之后,母女关系重新流动,女儿开始成长为“母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通过精神病的症状来重新理解妈妈,就像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恰恰是变化莫测的无意识而不是精心编码的意识,才是理解母亲的关键。
来自母亲的无意识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的不合情理和不可预测,面对偶然泄露的伪装,斜目而视或许能发现端倪,一旦主动捕捉,反而成了对母亲形象的再次框定。
2021年春节档,贾玲带来了她追忆母亲的导演首作《你好,李焕英》,这个感人的故事最终收获了54亿票房,让贾玲出道即巅峰,成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女导演。
在母亲李焕英发生意外的弥留之际,女儿贾晓玲穿越回了母亲的青春时代,她决定帮李焕英改变命运。
几经波折命运依旧,在离开之际她才意识到,不是她在帮助李焕英,而是李焕英一直在成全她的帮助。
对于重视家庭伦理且崇尚地母精神的中国观众而言,李焕英对女儿的爱与包容让人很难不动情。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看起来影片最动人的就是李焕英对贾晓玲知情不报的“再次付出”,但真正的重点却在“知情不报”,对于女儿而言,母亲的付出只能是也必须是无言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女儿的意愿重新讲述的母亲故事,也是一个排除了母亲的母亲故事。
在这里,想象母亲如何伟大透露的恰恰是女儿的无意识,妈妈请你像从前一样,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与李焕英迥然不同的是,在《失去的女儿》中,莱达是一个没有女儿的母亲,女儿只在她的回忆里、描述里和手机里。
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没有母亲的母亲故事激发了广泛的共情,每个人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打动自己的细节,没有女儿的母亲故事却疑点重重,面对莱达这样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观众更想做的还是破案:面具为什么不见了?
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母亲的处境,与其说母亲总是处于某种关系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母亲总是对象性的,服从母亲叙事就是成为欲望对象,只有成为欲望对象,才能召唤属于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还有归还母亲主体性的可能性吗?
这或许是吉伦哈尔和莱达共同的疑问。
这也是莱达症状的真正由来,为了拒绝成为欲望对象的母亲,宁愿释放“本它”[5],让面具背后的另一个我显影。
到这里,我们虽然理解了莱达的不同,但偷拿玩偶的一系列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解读。
影片中给埃琳娜带来陪伴和安全感的玩偶,一旦到了莱达手里,就成了诡异之物(the uncanny)。
无论是从玩偶中爬出的虫子、流出的黑水,还是莱达对待玩偶的方式——她不过是像埃琳娜一样,让玩偶成为了自己的陪伴物——都让人察觉到一种诡异的氛围。
但显然,诡异的并不是玩偶本身。
玩偶之所以能触发诡异,是因为它暴露了莱达的被压抑的爱正在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向她回归。
这也是诡异物的真正含义,它原本不过是普通之物,只因为承担了无意识的伪装才压抑变形,显得诡异。
相比藏玩偶,更值得琢磨的是反复藏玩偶,即使被管理员看见了,莱达也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归还玩偶的那一刻总是被延迟。
也因此,我们需要为莱达的症状重新正名,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始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就是说,掩藏玩偶的强迫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才是莱达真正的症状。
通过回忆我们得知,莱达曾经把自己儿时心爱的玩偶作为礼物送给大女儿,但大女儿却因为得不到关注,就把玩偶看作母亲的替身加以报复,用彩笔画得乱七八糟。
暴怒的莱达为了惩罚女儿把玩偶扔出窗外,玩偶碎了一地。
如果把从海滩带回的玩偶看作是被摔碎玩偶的替身,那么清洗的确是一种象征性修复,我们猜测莱达也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现场。
但更重要的是,清洗并不是终点,在妮娜一家到处找娃娃,家族众人对她充满敌视的情况下,莱达还是冒险去店里买了物料,给娃娃换上了新的衣服。
焕然一新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玩偶还给自己,而不是女儿。
只有以莱达为目的,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带走玩偶的真正意义。
带走玩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召回新手妈妈的焦虑,这才是莱达想回到的现场。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反复回到创伤场景虽然不合情理,但仍然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变体:通过不断重返,主体把被动创伤变为主动体验,从不可控变为可控,从不愉快变为愉快。
也就是说,莱达想要回到现场的原因,也许和我们预想的正相反,要修复和控制的不是女儿的创伤,而是作为母亲的自己。
失去的女儿到底是谁,是影片留给我们的最后疑问。
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多重关系的指代,在每一对母女关系中都有一个失去的女儿,对茫然的莱达而言,这个女儿其实是她自己。
这么说当然没错,只是或许仍然难以抵达没有面具的真相。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失去的女儿”并没有任何隐喻,在摔碎玩偶的那一刻莱达和女儿都遭遇了情感危机,那一刻她的确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对女儿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女儿的依恋——这让她感到十分遗憾。
但更遗憾的是,她并不后悔。
莱达既没有后悔成为母亲,也没有后悔在那一刻离开女儿,这才是故事的残酷真相。
这也是我没有沿用豆瓣译名《暗处的女儿》的原因,让母亲离开隐喻,或许能看到更多。
莱达和妮娜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影片中也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莱达对妮娜的关注看作是母亲之爱的移情,那么妮娜对莱达的诉求仍然是欲望对象的投射,因此这种召唤注定失败。
归还玩偶的惨烈场景也向我们说明,摔碎的玩偶已不可能再还给女儿,只能还给自己。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离开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原谅她之前,她可以自己原谅自己吗?
这或许是《失去的女儿》留给观众的真正难题。
此时此刻回头再看莱达,或许我们可以赞同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吧!
”(Enjoy your symptom!
)。
本文已发表于《戏剧影视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1] 数据查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
[2] Elena Ferrante, The Lost Daughter. New York: Europa Editions, 2008. Translation by Ann Goldstein.[3] [意]埃莱娜·费兰特:《碎片》,陈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第44页。
引用版本来自得到电子书。
[4] Richard Brody, Maggie Gyllenhaal’s “The Lost Daughter” Is Sluggish, Spotty,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the-front-row/maggie-gyllenhaals-the-lost-daughter-is-sluggish-spotty-and-a-major-achievement, 2022-1-3.[5] 弗洛伊德的著作The Ego and the Id通常被翻译为《自我与本我》,但近年来已有译者提出译作“本它”更接近id的德语原文Es,也更能突显自我对本它的“入侵”。
参见《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唐健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8 ) 我是不正常的妈妈 但我爱我的女儿
若按罗兰·巴特所说,“写作就是提出问题”,那么,由美国女导演玛吉·吉伦哈尔执导,改编自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暗处的女儿》,就是以视听语言的形式再一次将“母性”和“母女关系”问题抛给观众的勇敢尝试。
从小说到电影,《暗处的女儿》是如何延续费兰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的?
它又如何通过“最背叛却也是最忠实的”改编,重新打开了“母亲”背后的迷思?
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张雁南,编辑丨罗皓菱,首发于《北京青年报》3月11日青影院B03夏日假期的海滩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电影,大多是从“女儿”回望“母亲”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杨荔钠的《春潮》,瑟琳·席安玛的《小妈妈》,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以及马里奥·马尔托内执导,改编自费兰特同名小说的电影《烦人的爱》。
尽管“回望”的动机往往在于女儿自身成为了母亲,体验到身为母亲的种种,因此想要重溯与母亲的关系(杜拉斯说,既是歌颂也是清算);尽管在“回望”过程中也会暗示与下一代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无论从篇幅还是强度上来看,母女关系中的母亲和母性维度,仍处在隐而不显的晦暗状态中。
如何理解这心照不宣的缄默?
或许是我们早已预感到,比起女儿的回望,以母亲作为第一视角,在无限贴近自身、反思自身的过程中触探母性和母女关系,无疑是一桩更艰难也更凶险的事件。
但为了孕生新事物,为了在影像中缝合母亲的碎片,电影《暗处的女儿》便在标记为“母亲”的暗礁处惊险地起航了,径直驶向的是费兰特世界中一处最关键的时空图景:女主角莱达独自前往度过夏日假期的那片海滩。
夏日假期,意味着日常生活秩序的中断,意味着剧场的幕间休息;飞沙走石的海滩,是海陆之间的居间地带,也是海洋法与陆地法之间的交界处。
海滩一开始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排排静待人物入场的沙滩椅。
48岁的莱达载着半箱书稿,计划在那里安排她的工作假期。
穿过松林抵达海滩,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本能地将自己浸泡在海水里,作为从身份到身体的仪式性转换。
女性身体在场的恢复,也改变了身体与周遭的关系。
在模糊了社会身份和父性环境的意义上,现实中的夏日海滩便翻转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母性空间。
松林气息的吹拂环绕,海浪的轻拍和律动,海滩全然地裹拥着遮阳伞下的莱达进行阅读和写作。
然而,夏日海滩的空与静不仅没能持续多久,搅扰人心的旋涡更难以被阻挡在墨镜之外,入侵者的声音早在目光锁定之前就刺入了莱达的耳蜗:先是从海滩另一头哗然而至的那不勒斯大家族,接着是从海上驶来的那不勒斯青年男女的摩托艇。
外部声音的灌入触发了莱达心中某种莫名的紧张和焦虑。
当她试图在海滩上追踪陌异感的来源时,莱达的目光落在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身上:因为她脱离家族只和女儿埃莱娜做伴;也因为她的沉默和异域风情,使其难以融入那不勒斯家族的全景之中。
对妮娜的远景式观察,在莱达心中唤起一种女性处境意义上的相似感,面对妮娜,莱达开始联想起初为人母时年轻的自己。
果盘暗处的秘密声音的侵入刺破了宁静假日的想象,但早在莱达抵达海滨旅馆时,事件性的可怖征兆就已经在餐桌上的果盘暗处静候着她了。
只不过一开始莱达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为一名游客(观众)进入虚构的科佩里岛(剧场),并不会留意暗处的危险;此外,对知识女性身份的认同也担保了莱达的客观视角,为此她认真纠正管理员莱尔对她的猜测:我是一名大学教授。
不过第二天,当莱达在海滩上遇见那不勒斯家族和妮娜,目睹了她和女儿、娃娃之间的互动时,一股眩晕感就像灯塔的煞白之光那样射入她的身体。
正是主体晃动的时刻,当莱达想要以水果充饥时,她命运般地撞见了水果的腐烂内核。
鲜亮果盘的陡然翻转,像是骤降的暴风雨倾覆了平稳航行的船只,暴露出知识的无能和身份的脆弱。
实际上,要是母女关系真能通过这套父权象征体系而被阐述清楚,要是所谓母性的“原罪”真能通过控诉父亲们在育儿上的心照不宣而得以被彻底清算,要是千百年来女人-母亲的私人痛苦真能通过反转传统家庭性别分工,像男人那样牺牲家庭、追求事业、享受自由,像父亲那样育孩(几通简短、无关痛痒的电话,满足女儿的非情感性需求)而得以解决,那么《暗处的女儿》就不必存在,也无需被改编了。
但《暗处的女儿》的深意正在于,它将腐烂的果盘进一步翻转成了母性欲望的生产性标记。
正是在丑陋、扭曲的否定面向上,莱达认出了被压抑至今的母性欲望。
也正是这疯狂涌出的欲望,将她从观众席卷入到舞台中央。
如果说在果盘事件发生之前,莱达与妮娜之间的关联只是基于一种笼统的女性经验的相似性,那么在经历了种种陌异征兆(母蝉、松果、暴风雨)之后,在一种更隐秘的母女关系维度上,莱达与妮娜之间形成了一条强韧纽带:莱达看见了“年轻完美母亲形象”背后那个因疲于安抚女儿情绪、因女儿和娃娃的失踪而痛苦的女人,那个为了享乐和自由而和海滩服务生威尔偷情的女人;而当莱达回忆起初为人母时的情景时,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节。
与此同时,随着“母亲”秘密的陆续敞露,莱达似乎更危险地卷入到妮娜和埃莱娜之间。
她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母女之间的汹涌欲望:女儿的渴求与忧伤、母亲的野蛮与疯狂、母女之间的彼此享乐与彼此吞噬。
频繁出现的焦躁和头晕,正是莱达心理防御机制启动时的身体性症状。
抛来抛去的娃娃影片中唯一成问题的物件就是娃娃。
若果盘在事件的意义上揭开了“母亲”的暗处,启动了性差异的开端,那么,随妮娜和埃莱娜一同出现的娃娃,也就不能再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女孩玩具。
它是清空了一切涵义的空洞之物,因此才会被投射和移情,才会被莱达偷走。
但从性差异的角度来看,投射和移情之所以会触动,更是因为娃娃作为一种直接的中介,总是处在女性欲望、母性欲望的原初场景中: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母女是全然一体、互为彼此的,但父法的介入会分裂母女的粘连状态,造成母女的分离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
母亲深知这一焦虑和恐惧,因此拿出一个娃娃作为彼此的替代物。
至此,对女儿来说娃娃就是妈妈,对妈妈来说娃娃就是女儿,娃娃既是妈妈又是女儿。
在替代和分身的意义上,丢失的女儿或娃娃,无论对母亲还是对女儿来说才是一项绝对恐怖的死亡经验。
但母女之间的分身游戏远非止步于此。
露西·伊利格瑞曾描绘过一幅母女关系的动态图像,她说,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接抛球游戏,来回抛接着母亲与女儿既相似又差异的重重图像(image)。
相对容易辨认的是相似性的欲望,在影片中,经由母女彼此相像的身体,以及名字这一外部的相似性所担保;与此同时,娃娃内在地也是母女之间彼此“成为”(becoming)的通道:女儿想变成妈妈,莱达的大女儿比安卡爱观察和模仿莱达的小动作,她想像妈妈那样削出不间断的果皮;妈妈也想重新成为女儿,莱达会想象自己是比安卡或小女儿玛莎,像她们那样和年轻男士交谈。
正是在无限生成“妈妈-女儿”、“女儿-妈妈”图像的过程中,母女关系的否定性涵义才能被肯定性地改写,女性谱系才可能在母女之间编织起来。
这样的女性谱系超越了线性时间和物理空间,隐秘而又强韧地显现在一代代母女的生命活动之中。
48岁的莱达正是在女性谱系的意义上领悟了母亲突然站立时的头晕,女儿比安卡抵抗剥夺感的性格,以及祖母别戴帽针的方式。
影片结尾看似回归到影片最初的场景,莱达晕倒在深夜的海边,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清晨,海浪的拍打唤醒了莱达,她突然想到女儿们。
在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莱达接通了女儿们的电话,一边听女儿们的声音,一边剥着果皮,同时回想曾经和她们一起削果皮的场景。
海滩全景中,莱达半摇晃着的身体就像一只娃娃,在死亡与新生之后,重新找回了自身之中的女儿-母亲。
从此,一代代母女之间的精神线谱,就既像母女手中那条削不断的果皮,可爱可怖一如蛇怪海怪,更是涌动在母女之间的那条剪不断的脐带,自由纷扬在暴风雨的夏日海滩。
9 ) 母亲不是天然的
虽然母亲是自然赋予的角色,但没有一个母亲是天然的母亲。
看完后我主要想说的是…为母则刚,希望承担母亲的责任,享受孩儿伏在膝上的温暖也好; 不舍自由,热爱独处,害怕麻烦也罢。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误。
需要避免的是“违心”和“善变”…女人要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不要心中向往自由却又早早生下孩子,财力不佳却意外诞子,这是违背人心的。
如此,你不会快乐,孩子或许也不会快乐。
就像片中主人公一样不舍的追逐梦想 时刻觉得孩子是累赘……也不要过于善变,一会想要抛弃孩子,一会又想念他们…时机总是不对 错过的时光也不会倒回 你永远在后悔。
10 ) 关系
我发现全世界的女性(不包含战争、贫困国家等等)面临的问题似乎出奇的一致:我到底是谁?
我是某个家庭的女儿,像女主说的,“从我那个烂环境里出来”。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意味着要承担生育,以及绝大部分的养育。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情人,当生活像不断尖叫着打断你的孩子那样拽着你的头发,你只想抓一个温存的时刻,这个时刻让你对自己重新获得了掌控感。
可能我是某个人的母亲,意味着我要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个极不成熟的人带来的一切:无休止的尖叫、不间断的打闹、源源不断的精力、人的嫉妒自私霸占等等恶习。
那我到底是谁?
以及这么多的角色,谁给了他们定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在孩子打我的时候永远保持微笑吗?
我是不是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泄气和疲惫?
我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家庭的牺牲者?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如果“牺牲”意味着牺牲自己作为进化到成熟人类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时间、事业、金钱、容貌、等等等等,来抚育另一个从0起步的不成熟人类?
女人好像永远在这些角色里挣扎,就像电影里的每个女人,都想被困在某个无形的笼子里。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抛弃家庭?
女主因为工作离家三年,她为此止不住地流眼泪,她说那段时间fantastic,但为什么哭呢?
为自己感觉fantastic而认为自己不该有那种想法吗?
女人为什么永远的矛头对准的都是自己的心脏?
我猜测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低了,而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
“社会”的要求,让你说不出来是谁在要求,要求来自哪里,但是你,你自己,你丈夫,你婆家人,你娘家人,你朋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在心里暗示自己说,如果我这么做,ta一定会谴责我。
去谴责男人吧。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大人通过被无知的小孩一直敲脑袋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成长,为什么不能敲父亲的脑袋?
我那天看到有讨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与其他的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一样的,也 应该有关系的认知、讨论、实践,但是人往往认为这是天然的。
我认为“天然的母爱”也是一种绑架。
美国电影已经在这种关系上的讨论向内求索至此,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讨论?
女主非常棒,非常有电影演员的美,无关年龄,无关身材,就是真实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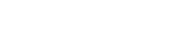

































Dickon Hinchliffe的原声带好到不像话。
讽刺的是,看这部片就被我儿子的各种琐事打断好多次,即便断断续续,这种“快要窒息”的育儿代入感,只增不减……曾经心里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是不是该扔下孩子,跑去山顶或者海边,大喊几声,或者后悔当个妈妈,最后还是对“责任”要妥协……这个世界,给当了“母亲”的女人的枷锁太沉了。
影片聚焦女性育儿的焦虑抑郁,刻画一个放弃责任,追求自我的女性角色,但压抑的影像风格和故事的推进缺乏说服力,更别提代入情感。或许是个人无法共情,或许是讲述太过无力,只记住了演员脸上无需铺垫突然泪目的表情
放过女性议题吧
女性导演才能拍出的作品,当一名女性不履行母职时将遭受什么。丈夫的威胁,情人的规劝,自我的负罪与愧疚(甚至愿意以死赎罪),以及本片男性观影者轻描淡写评价的一句“浪的代价”。
英国女王与查尔斯王子
看了30分钟,没有看出啥名堂。#20240626
纪录片
为母应逃。
又碎又乱,剧本和导演水准都不过关。
四星半,意外得不错,把现下社会文化领域几乎已经成为的常识但对很大一部分人(尤其男性)来说仍然较为抽象的议题内化回了具体的一段生命经验,这种实现又完全依托于电影语言的探索,除了非常统一的视线和肢体触感的画面整合,还尝试了多样的声画处理手段,通过视听合约的打破还原颅内记忆的突现、起伏、间断等复杂流动的意识活动,新导演做到这种程度很棒了。科尔曼可以再有一个影后。
不太确定导演是否知道自己要什么。和拉扎罗用同一个摄影,和兰斯莫斯的宠爱/normalpeople用同样的演员,如此强大的处女作阵容,制作出来如此散碎的叙事,实在让人难以啃下这块资本的蛋糕。无处不在的扰人配乐,为沉重而沉重,为压抑而压抑,女性力量不是抱怨谴责或娇嗔,我们有我们不依附于男权中心社会的活法。
m2201:开始以旁观者观望别人的幸福,挺感触。希腊线偏弱。奥利维亚和杰西演技赞。插曲《Let Me Tell You All About It》、《livin on a prayer》、《Stala》/Monika
把文艺片的刻板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莫名其妙的精神病主角 故作高深的台词和画面 配乐还挺好听 本来还因为没看成现场的导演讲座感觉很遗憾 现在很庆幸还好没去看
靠表演撑起来的电影,关于责任关于婚姻的探讨都流于表面,最后母女间的和解也显得突兀。
不好看啊,看的难受,看到这些不适合做母亲的做母亲就不太舒适。
威尼斯主竞赛第六场,昨天在看了《斯宾塞》和《沙丘》之后观看这部片时我已经意兴阑珊了,完全是靠着原著作者埃莱娜费兰特的名字坚持看完的。对演员当导演我一向不看好,导演的门槛真的好低哦。我不知道原著如何但对于电影给我的感觉女性意识强烈到让我不适,在我眼里这就是责任感缺失。众所周知威尼斯主竞赛一向是虎头蛇尾,后面的主竞赛影片我毫无期待。
靠演员抬出了原作里subtle的东西 处女作加一星
这个电影应该叫 real motherhood
实在是不喜欢这种镜头语言,接受无能